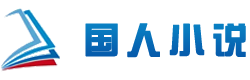2~4
2.
我又活了。
咦?我为什么要说又?我以前死过吗?
不对,人偶有生命吗?
你没有看错,我是个人偶,把我制造出来的人是云盟最牛逼的工匠。
他平时打造的都是神兵利器,一双手巧夺天工,很多人跪求他给自己造个东西,都请不动他,可是在那个云盟掌门的威逼利诱下,他终究是为了小命着想,用那双神手把我造了出来。
然后在我睁开眼睛,犹豫着要不要按着传统套路对着眼前这个独眼男人叫一声爹爹的时候,他伸出五指招手一个大嘴巴子又把我给抽晕了过去。
其实事后想想,他这么做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曾经都是给大老爷们儿制造暴强的法器,一把剑都能斩断山河的那种,结果让他用这双手造出了一个娘炮,还是裸的,这心里多少都会不舒服。
其实我不喜欢用娘炮来称呼自己,但第一次照镜子的时候,忽略脸上的五个手指头印,又对比开门进来给我准备衣服的侍女,我觉得长成这样实在是太难为情了。
由此可以看出那工匠也不是什么好鸟,把我做这么好看有个毛用?手无缚鸡之力,走两步都喘,打那一巴掌愣是肿了一个礼拜才好。
不过在我肿着脸的一个礼拜里都没看到那个工匠,下次看到他的时候,他两边脸都肿的没了形状,那个用来罩着瞎眼的眼罩都被肿起的肉给挤得堆了起来。
他看着我的表情异常惊恐,就好像我这个走两步都喘的人,呼出一口气都能把他吹死一样。
“你没事吧?”我很关切地问他。
“啊!啊啊啊!”谁知道我走近一步,他就叫唤一声,到最后就这么踉跄着跑出了门。
额......所以说他来这里是干嘛的?
而且为什么这么怕我?打我的人不是他吗?
“祁让。”随着他出门,有个人走了进来,穿着讲究,长得也好看,比我高了半头,往我这边走的时候让我相当有压迫感。
说实话,我有点害怕这个人,这倒不是我的思想,是这具身体反映给我的本能感觉。
我往后退了一大步,拉开两个人的距离,又看看四周,确定一个人都没有,才问他,“祁让是我的名字?”
然后他就愣住了。
而且愣住的时间相当长,长到我无聊的用一个手指甲去抠另一个指甲里的灰。
抠完整整十个指甲的时候,那个人才从漫长的沉默中醒过来,对我说了第二句话,“嗯,祁让是你的名字。”
......????
就这么一句话用得着想这么半天吗?这人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看他这傻了吧唧的样子,我心里倒是没有那么害怕了。站累了就干脆一屁股坐到了床上,倚着床栏杆,懒洋洋地问他,“那你是谁啊?找我什么事?”
又是一段长到让我想继续抠指甲的沉默之后,眼前的男人才酝酿好感情,眼圈通红地对我说了第三句话,“我叫萧阳。”
“哦,萧阳啊。”我将他的名字在嘴里嘟囔了一圈,然后瞬间瞪大眼睛,起身慌里慌张地给他行礼,“小的不知道您是云盟掌门,刚才有失礼的地方,还请您见谅!”
艾玛,这下完蛋了,我竟然在大名鼎鼎的云盟掌门面前抠指甲,这是多么的不知死活啊!
短短时间,我已经开始思考我这个倒霉的人偶要怎么被回炉重造了。先把胳膊腿儿都摘掉,然后卸脑袋,再然后把肚子破开,内丹拿出来......
“你不用怕我。”谁知道下一秒,眼前一道阴影靠近,我便被这个叫做萧阳的男人给抱进了怀里,紧的让我呼吸困难,甚至想翻个白眼。
就在我昏昏沉沉,以为自己要成为第一个被云盟掌门抱死的男人的时候,听到他说,“祁让,我好想你。”
我没空去思考他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再下一秒我已经没了知觉,生生被这个脑子有病的男人给用那看着并不粗壮却力道十足的胳膊给勒晕了过去。
3.
大家好,我叫祁让,是一个走两步都觉得身体透支的病秧子人偶。
自从被俊俏的云盟盟主给搂晕了之后,我就被安置到了他的寝殿里,每天和他住在一起,并且要听话的张开嘴巴一口一口地从这个男人手里的勺子里舔药喝。
这种事发生在两个男人之间怎么看怎么矫情,但对方是辣个站在当今六界实力顶峰的男人,我是万万不敢以下犯上对人家说“我虽然虚的不行,但我胳膊腿儿没少啊,喝药还是会的。”这种彰显骨气的话。
所以发展到现在,他递勺,我张嘴,他给糖,我傻笑,他拿起手帕给我擦嘴,我就特享受地任由他细心地伺候我。
啊,这该死的惯性。
后来我从走两步就喘进步成走十步喘的时候,萧阳终于善心大发放我出去玩耍了。
但前提是他要跟着我,而且还得固执地和我保持着手牵手的姿势,我象征性地挣脱了下,没挣开,翻了个白眼也就随他去了。
毕竟人家是牛逼的盟主,他要是心里一个不高兴就把我回炉重造了怎么办?
不过出去之后我就发现这家伙更奇怪了。
这座宫殿很大,有很多回廊和花园,我作为一只吃饱了就睡思维简单的人偶,本来见着这么复杂的布局就够头疼了,身边这位却总是见着一个地方就给我指,问我,“你还记得这里吗?”“你还记得那里吗?”“这里有印象吗?”“那里呢?”
比如今天我和他走到一处小亭子坐下,亭子下面是一片空旷的小花园。
这个男人看着下面发了会儿呆,然后突然目光灼灼地问我,“祁让,你还记得吗?当初你就是在这里教我如何用剑的。”
他站到我坐的椅子后面,两只手从我的肩膀处绕过来,然后抓着我的胳膊,摆成一个在我看来非常奇葩的动作,说,“这是风煞剑的起手式,你说明明是很霸气的动作,我每次做起来都让你很想笑。”
“哈,哈哈......”针对这样古怪的发言,我用我思维简单的大脑猜测我应该配合他笑两声。
可是我笑完之后只觉得尴尬,然后开始深刻反思是这个萧阳有病还是我有病。
背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动静,直到眼前寒光一闪,接着一个冰凉的剑柄便被萧阳送进了我的手心里。
“站起来。”男人的声音里没有笑意,我听着都觉得吓人,赶紧听话地站起来。
“拿着那把剑与我交手。”
“萧盟主,这,我......”我被他这命令吓得六神无主,恨不得当场归西。
我一个没有修为,只有个病恹恹空壳的人偶哪能和他交手!那不是自取灭亡吗!
他要是想让我回炉重造就直白地说啊!为啥拐弯抹角,非得亲手把我砍死才满意?!
“傻站着做什么?”萧阳的眼神冰冷,语气有些急躁,“我让你挥剑!向我挥剑!”
“好......好吧。”我心里打着突突,握着剑的胳膊抖个不停。
最后两眼一闭,使出浑身的劲儿举起手里的剑向着萧阳挥过去。
然后......啪叽一下踩到袍子的下摆,在这个喜怒无常的男人面前结结实实地摔了个狗吃屎。
空气凝滞了好几秒,我生无可恋地趴在地上捂住流血的鼻子,面对着近在咫尺的黑靴子,觉得自己相当丢人。
“你不是祁让。”头顶的男人终于发话,却是带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低气压,我清楚地听到他说,“祁让早就不在了,他早就不在了......”
他重复了几遍这句话,声音里是难以掩盖的哽咽。
然后在我思考着要不要爬起来去安慰安慰他的时候,抬起大脚,迈开大步,毫不留恋地走出了亭子,把我这个还在流鼻血的倒霉人偶丢在了这里。
......果然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4.
我目送他走远,赶紧爬起来,搓了搓身上的袍子。
毕竟快入秋了,天冷,这地上也凉飕飕的,待时间长了我可能又要得病了。
其实我挺疑惑的,就很想找个时间来问问那个工匠,为什么您那双能制作出神兵利器的手做出的人偶会这么弱?
讲道理,我不是应该很强嘛?不说是能打得过谁吧,至少不应该身体不协调到走个路都会踩到袍子吧?
刚才简直要丢死个人了......
我当时觉得事情的发展应该是,我握着剑哐当和萧阳手里的剑来个亲密接触,可怎么就废物到变成啪叽一下摔地上了呢?
挠了挠脑袋,我捏起衣服袖子,把自己脸上的鼻血擦干净,然后低头看了眼脚边的剑。
很朴素的一把剑,没什么装饰,剑柄也不宽,我把它捡起来,恰巧看到在剑身底部和剑柄之间的地方,刻着三个小字。
“赠萧阳”。
前一阵萧阳教会了我识文断字,而且着重让我记住了他名字的写法,所以此时我清楚地了解这三个字的意思。
说了赠萧阳的话,那这应该就是那家伙的专属佩剑吧?
到底生多大的气,跑的倒是挺快,连剑都不要了。
不过他今天说的话也挺奇怪的,他明明说了我叫祁让,刚才那态度却又像是在说他和祁让曾经经历过的事。
所以我现在猜测我这个人偶应该是那个叫祁让的替身,萧阳给我起这个名字就是想从我找到那个人的影子。
当别人替身什么的,真有点不爽。
回头要不要和掌门大人商量着能不能改名啊,毕竟经过今天这件事,对方应该不会再把自己这个菜鸡和那个祁让想到一起去了。
我往前走了两步,感觉膝盖有点疼,卷起裤子腿,发现破了一大块皮,顿时觉得头疼。
搓了点唾沫上去,我保持着卷着裤腿的姿态,杵着长剑往回走,心里隐隐期待今天小荷会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
结果从下午走到晚上,直到膝盖上的伤口结了一层痂,我都没找到自己住的地方。
而且沿途竟然一个人都没遇到!
随着变黑的天色而来的,还有毛毛细雨。
我一开始没在乎这点小雨,结果淋得透心凉,连打了几个喷嚏之后,发现这副身体果然是不能用普通的弱鸡来形容,这简直是弱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
脑袋有些犯晕,我走到有回廊的地方,缩在屋子边缘避雨,却并不进屋。
我在想万一待会儿有人过来找我,让我错过了怎么办?
所以本着这个念头,我就给自己整理出一个地方,倚靠着墙壁,看雨水从房檐上滴落。
一滴,两滴,一串,两串......
明明身上很冷,脸却很热,头疼的很厉害,我眼前的景象都是模糊的。
意识仿佛神游天外,直到一个身影遮挡了背后的雨幕,我才迷迷糊糊地抬头,对那人勾了勾嘴角。
下意识地吐出一句话。
“阳阳,你终于来找我了。”
空气安静了好久,就在我以为自己眼前的人是幻觉的时候,下巴猛地被扣住,唇上传来柔软的触感,使得我被高烧弄的意识模糊的大脑彻底化作一团浆糊,停止了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