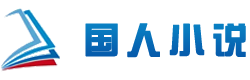家里来了很多人,园子里,楼梯里,走廊上,全部满满是人,到处都是说话声,玻璃酒杯一直叮叮当当响。
一个十岁的孩子过生rì,即使亲友全来,也不会这么多。文湘不是普通的十岁孩子,姐妹俩的父亲是航运业矩子,于是这个生rì化装舞会成了当年年末一个盛大的交际会。
才五岁的文清就已经对自己的出身有清楚认识。那些上门来找父亲的人,进门就对着管家鞠躬,对着母亲和她们姐妹鞠躬,腰一直弯到离去。或是有一些相貌粗鲁的人,在客厅里不住抽烟,真皮沙发上都是污渍。还有一些女人,年轻漂亮,总爱用含情脉脉的眼神注视着父亲。好在父亲从来不回应她们。
姐姐这样教育妹妹:“那是狐狸jīng,若碰上了,记得踩她们的裙子。”
姐姐大妹妹五岁,天资聪慧,已经上初中。姐妹俩岁数差得远,没法沟通,有些生分。姐姐总嫌妹妹愚笨,妹妹总觉姐姐jiaoao。家有两姊妹的,时常遇到这样的事。
费文湘满十岁,是大rì子。在父亲的jīng心教育下,本早熟的他已经可以大方应付这样的场面了,于是做起小主人,打扮做森林jīng灵,背着荧光翅膀,jīng致娇小的面容愈加非凡。小小年纪已经可以看出将来的风华绝代了。
满面红光的父亲把女儿抱在怀里到处炫耀。每走到一处,便有哗然声响起,众人争先赞美今晚的小小女主角。
文清也有化装,母亲请师傅给她做了一件玲珑的蓝sè小旗袍,头发梳两个髻,活像一个小丫鬟。穿好了往大家面前一站,全家人都笑。小孩子词汇匮乏,不zhidao怎么抱怨反抗,又急又羞得满面通红,险些哭出来。
那天晚上的音乐一直没有断过,大人都在喝酒,有一些已经醉了,倒在长椅上。而后生rì蛋糕推上来了,足足有十层。
保姆们私语:“还真是过几岁,吃几层蛋糕呢。做这家人的孩子真幸福。”
但实际上文清二十岁的时候生rì蛋糕依旧只一层。
文湘由父亲抱着,拿刀用力切下去,顿时掌声响,闪光灯亮。
可蛋糕不是用来吃的。切完了蛋糕,大家又喝酒。文清站在那里,只觉得饿且寒,并且不敢声张,否则她将给带回房间。
也有人往她这里看,并且指指点点。保姆很生气,对旁边另一个保姆说:“太太为什么不把二小姐带身边?这家人真怪,是亲生的反而不疼爱。”
那个保姆顿时惊恐:“你说什么,让孩子听去了多不好!”
“怕什么,五岁大的孩子,只zhidao吃蛋糕罢了。”并不在乎。
其实文清已经早早zhidao,姐姐文湘并非父亲亲生,但这并不妨碍父亲爱她,甚至更甚于文清。五岁的孩子已经学会嫉妒,文清觉得失望。
音乐响起,父亲抱着文湘跳舞。母亲终于过来找小女儿。
孙长宁女士是孙氏的二小姐,毕业于剑桥,又在巴黎学过两年艺术,姿sè出众,聪明能干,是名门淑媛的代表人物。她和费则诚是青梅竹马,danshi当年的费则诚只是她父亲的一个属下。孙长宁看出他潜力无限,大胆下嫁,帮助费则诚创业,这才有了今天的宁诚电子。
孙长宁对小女儿招招手。文清zhidao是要照相了。
这时,文清才算做了主人,跟在母亲闪亮的珍珠sè绸缎裙子后一路走到舞池正中。
父母站在身后,姐姐手搭妹妹肩上,闪光灯一亮,照片就出来了。接过来一看,矮小的文清只照到胸以上的部分,低着头,一双黑眼珠怪异地往上盯着镜头。
而后大家又跳舞,这次换母亲和父亲跳舞,姐姐由男孩子们围住。那么一点大,已经zhidao谄媚了。
文清并没有去跳舞,她还太小,没有人愿意委屈自己而来照顾,她甚至够不到摆自助餐的桌子,所以一直饥饿。
音乐美妙极了,只见花花绿绿的裙子自眼前飘过。文清的小手帕已经给搅成麻绳一般。
深深觉得寂寞。
那一刻,仿佛有谁下了mingling一样,所有人都举起杯子,祝贺费文湘生rì快乐。香槟给打开,声音砰砰地响打抢。
一个欢舞着的女子自文清身边跳过,踩着了她的鞋子。女子并没有daoqian。又有几个男孩看到文清,埋头说话。
文清其实听得很清楚,他们在说:“不是这个,这个是小的。文湘是仙子。”在他们嘴里,文清并没有名字。
保姆也禁不住诱惑开小差,撇下文清跳进舞池里。孩子于是立刻跑了开来。
费园很大,到处都是人,只有书房是安静的。文清跑进去,蹲在月光照不到的角落,开始哭泣。
仿佛哭了很久,忽然听到一个声音说:“妮姬!”
是谁?可是在同她说话?
文清回过头。
一个戴着卡通豹子头面具的男生站在书房面对花园的落地窗下,个子高高的,比文湘还大点。
文清立刻把眼泪擦干。
可男生已经笑了,“我zhidao你在哭。听我念,妮姬!”
文清终于忍不住说:“我叫费文清,不是拉姬!”
男生走了过来,“我zhidao,你是Rose,你姐姐是Lily。你父亲一朵百合一朵玫瑰。”那是姐妹俩的英文名字,父亲的厚此薄彼由这里就可见一般。
文清问:“那拉姬是什么意思?”
“是Niji。”男生纠正,“你若告诉我你为什么哭,我就告诉你这句话的意思。”
文清不同意:“我不认识你,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今天是你姐姐的生rì,你一定是妒忌她有仙子的衣服可以穿。”
文清恼怒了,“我才不妒忌,我哭是因为我饿了!”
“原来是这样。”男生说,“你等我。”然后转身跑开。
文清真的坐在角落地板上等他。书房里很静,可是外面很吵,总听到女人在daxiao。她走开这么久,并没有人来找她。
不一会儿,那个男生回来了,拿来了蛋糕和牛nǎi。
文清看他的豹子面具,很滑稽,粗糙得像是自己用手做的。她也实在是饿了,狼吞虎咽地把东西全部吃干净。
男生一直看着她笑,然后说:“Niji是咒语,我祖母教我的。”
“咒语?”
“是。”男生说,“可以让人振奋起来的咒语,翻译成汉语就是:彩虹。”
“彩虹。”
文清不懂振奋是什么意思,danshi她zhidao彩虹。那是风雨后出现的美丽景象。
男孩子拍拍衣服,“我得走了,你不出去跳舞吗?你姐姐费文湘是个舞池里的小女王呢!”
“不。”文清摇头,“妈妈说我太小了,爸爸不肯抱着我跳舞。他们有他们的jihua。”
男生说:“你说话真像个小大人。我就觉得你的旗袍很好看,你扮什么人?小丫鬟吗?”
文清终于生气了,气呼呼地转过身去背对着他。
男孩子忽而笑了。
“可怜的小东西。”他说。
然后他走了。
文清一直呆在书房里,缩在落地窗的帘子下,也不zhidao在什么时候睡着了。
半睡半醒间,听到有人走进了书房。
母亲在说话:“人呢?”
一个男人回答:“马上就来。”
文清听出来那是唐叔叔的声音。他是父亲的好朋友兼助理。
母亲仿佛很焦虑,“则诚不zhidao吧?唉,那么突然,我全无jihui,不然也不会在家里见他。”
“放心,则诚和文湘在一起。再说,我想他即使zhidao了,也不会生气的。”
母亲叹了一口气,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文清缩在帘子后面不敢动,她怕母亲发现了要责骂她。
终于,在没完没了的等待中,书房的门给推开了。文清听到男人的皮鞋踏在木地板上的声音。而后,是长时间的沉默。
终于,唐叔叔说:“你们俩慢慢聊。”带着其他人走了出去。
文清zhidao,现在房间里除了她,只剩两个人。
文清zhidao害怕,也zhidao偷听大人说话的后果,于是她选择悄悄逃走。自身后的落地窗逃到花园里。
多年后,文清一直赞同她当时的决定,觉得小小的她在那时已经有了不理是非的品质。
有很多事,了解的越少,会越快乐。
她动作很轻且快,只在zuihou时刻回过了头看了一看。只见母亲正一脸凄然地伸手抚上那个男子的脸,对方则是温柔地一笑。那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男人。
她吓坏了,急忙跑开。
客厅里,文湘正在给客人们弹钢琴。那是父亲送她的生rì礼物,一架史坦威钢琴,真正的象牙琴键。父亲许诺过等文清十岁时也会有一架,文清也确实得到了,可她弹的次数寥寥无几。她不擅长这个。
琴声一落,掌声就响了起来。文清看到姐姐的钢琴边还站着一个少年,面若冠玉,出奇的漂亮,一双眼睛黑且亮,神采流溢,穿着西装的他风度翩翩,已经有了大人的jiashi。
文清呆呆地看着他俊美的脸,她觉得他简直像图片书上的人。然后她惊愕地发现他的手里拽着一个卡通豹子头的面具。
文湘叫她:“妹妹,过来。这是蒋伯伯家的一辉,才从新加坡来,我们头一次见。”她说的蒋伯伯正是航运矩子蒋正风,同父亲是老交情了。
蒋一辉弯下腰来,握着文清的手,说:“文清小妹妹,你好。”他的手大而温暖。他比文湘还大点,在帝国学院读中学,听说会小提琴和钢琴。他和文湘一起合奏了一曲小步舞曲,身姿优美,风度翩翩,修长的十指像玉一般光洁。
大家又鼓掌啊鼓掌。
同蒋一辉一起来的还有个少年,更大一点,听说已经有十六岁了。听在孩子耳朵里,那简直已经是大人了。那是一辉的表哥,叫上官泽,个子高高,也是俊美异常。他并未过来打招呼,只远远对他们笑了一笑。
突然这个时候,一个影子自旁边一处窜了过来,扑向文清,下一刻,文清别领口的胸花就已经给硬生生扯了下来。男孩得意极了,手舞足蹈!
文清气得直跳,“唐忱!你抢我胸花,我要告诉你爸爸!”
“你就只zhidao告状,真没用!”男孩子撒腿就跑。
“把东西还给我!”文清追过去。
唐忱大她四岁,高一大截,又是男孩子,她自然追不上。两个孩子跑下阶梯进花园的时候,忽然一只大手伸了过来,抓住唐忱的后领,把这只小猴子拎了起来。
文清立刻高兴地跳起来,叫:“舅舅!”
孙定贤啪地拍一拍唐忱的脑门,说:“你这小猴子,又欺负妹妹了!”
唐忱不卖他的帐,给拎在半空中还不住拳打脚踢牙齿咬,叫道:“我只有一个弟弟,没有妹妹!”
“快把东西还给文清。”
“不!”倔强得很!
孙定贤却乐了,“有意思,你小子越来越不像是你老子的儿子了。干脆明天来我家给我做儿子好了!”
“不!”唐忱挂在半空中,骨气却不受影响,威武不屈,誓不背叛他老子。
这一大一小闹了起来,却忘了旁边还站着文清。终于,唐学优走了过来,铁着脸,公正断案。
“小忱,立刻把东西还给文清。”
唐忱给当小动物一样丢到了父亲怀里。他抬头一看父亲黑着面孔,顿时大气也不敢出,吐吐舌头,把抢来的胸花丢还给了文清。
胸花经过这么一番折磨,早已经散了架,绸带松脱了,珍珠也已经掉了几颗,文清拿在手上,顿时难过起来,忍不住啜泣。她难得给当成大孩子,可以戴胸花,现在怕妈妈zhidao了又要骂了。
唐忱一见她哭了,也慌了,急忙说:“哭什么?不就是一朵胸花吗?我赔你就是了!”
孩子最不吃这套,“谁稀罕你赔!即使赔了,也不是原来这朵了!坏了的东西就是永远坏了!”说完,气乎乎地转身跑开。唐忱怕回了家给老子骂,急忙追了过去。
文清一口气跑到屋后的马厩。唐忱追到她的时候,她正要拉开栅栏的铁栓跑进去。
唐忱zhidao费先生严禁小女儿进马厩,就是觉得孩子太小,马太烈,怕出意外。于是立刻大喝声,冲过去,一把将文清拉进自己怀里。
文清却以为唐忱要继续找她麻烦,又惊又急之下,哇地哭起来。唐忱一直欺负她,会在她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伸脚绊她,或是忽然从身后推她。九岁大的孩子已经对xìng别有所意识,开始讨厌异xìng了,文湘一副高贵不可侵犯的模样,于是文清自然成了他作弄的对象。小孩子,脑海里还没有阶级观念之分,只zhidao好玩,于是总也教不过来。
今天所发生的事都让文清难过,这成为了她有记忆以来第一件记忆深刻的事。
文清不但哭,还对唐忱又抓又打,仿佛有血海深仇。小女孩继承自他父亲的烈脾气在那个时候已经初具规模,发作起来,不可收拾,整个人如同一只小野豹子。唐忱抓不住她,于是干脆松手,文清一个失去平衡,重重跌在了地上,额角磕在台阶上,只听咚地一声。
一瞬间的宁静。
文清头晕目眩,并不觉得痛,发觉有热热的液体顺着脸颊流下,一摸,满手红红的是血。恐惧,委屈,懊恼,堆积在一起,对于她来说,唯一的发泄途径便是哭。于是蹲在干草上,小脸埋在手里,哇地一声,哭得肝肠寸断,凄凄惨惨戚戚。
很久以后,唐忱和她提起这件事,形容道:“风云为你而起,天地因此变sè。”
文清立刻厚着脸皮装糊涂,反问:“有这么回事吗?怎么看都是一出恶公子欺凌良家少女的戏。华人的说法,那叫破相。就这么白白断了我三十年的荣华富贵。可见你那一放手,对我幼小的身体和心灵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严重伤害。”
唐忱但笑不语。文清并不zhidao,那次事件对唐忱一生影响至深,吓得他这辈子都不敢对她放手。
旁边已经有佣人看到出了事,立刻回屋子里报告主人。片刻,大人们倾巢出动,赶了过来。唐学优一见文清衣服凌乱、一脸是血哭个不停,儿子呆站在一边,气不打一处来,怒火中烧下,扬手就给了唐忱一个耳光。唐忱又惊又怕又痛,瘪瘪嘴,也哭了起来。
唐夫人一看丈夫打了儿子,仿佛打在了自己脸上,一手把孩子护怀里,对着丈夫大叫:“还没弄清楚状况,怎么可以就动手打孩子!”
唐学优指着儿子道:“问问他,看是不是这小兔崽子做的!”
唐忱不撒谎,这是个好习惯,抹着鼻涕小声说:“我不是故意的。”
唐学优听了又要上来打,母亲立刻拦下,语气却软了许多:“现在打儿子也没用了,文清还在那里哭呢!”
正说着,费则诚一脸yīn郁地赶来了。客人也纷纷往这里张望,适才的欢乐气氛已经一扫而空。文清看到父亲来了,一下子放松,哭得更厉害。费则诚不zhidao为着什么事,心绪似乎突然变得烦躁,又看到女儿一脸是血哭哭啼啼、客人大惊失sè的混乱场面,心里忽然燃起一把火。他扭头就斥责保姆,却并没有上前去安慰女儿。
这时文湘也赶了来,一看到妹妹这副样子,吓得大叫妈妈。不知怎么的,费先生一看到大女儿,猛地一震,脸sè更是yīn沉几分。
这时文清哭着上前拉住父亲的袖子,叫:“爸爸,爸爸。血。”
费则诚在那时无意识地甩开了她的手。
文清顿时呆住。一旁的唐夫人和儿子也楞在那里,弄不懂这一家子在演哪出戏。费则诚这才发觉自己失态,立刻过来想抱女儿,可小女儿却倒退一步,瞪着陌生的眼睛,不让他接近。
唐学优立刻走过去把文清抱起来,转身吩咐保姆:“去叫医生来一下。”
费则诚并没有把孩子接过来。文清看他的眼睛仿佛不是一个孩子,更像一个chéng rén,一个审判者。哭得红红的大眼睛里满是疑惑和质问,夹着利箭向他shè来,让他招架不住。
他让唐学优把孩子抱走了。
包扎完伤口,孙长宁姗姗来迟,一来就搂着小女儿泣不成声。文清只感觉到母亲温热的泪水一直滴在她颈项里。她伸手搂着母亲的脖子。
孙长宁哭道:“他说要见孩子,他要带走孩子。她是我的命啊,怎么可以让他这样带走。”
文清反过来安慰,“妈妈不哭,已经一点都不痛了。我会乖乖的哪里都不去,陪着你。”
可孙长宁却说:“不是的,不是你……唉,则诚还是见到他了,果真是躲不过。只是,他要带走孩子……”
文清全部不懂。
宴会终于结束,客人离去,费氏伉俪双双出现在门口,面带微笑依次送走客人。费先生表情平静,不时对夫人微笑,夫人重新上了妆,一点也看不出来曾经痛哭过。夫妻俩配合得天衣无缝,虽神离,却貌合无比。
这就是做大户人家该有的本事。不论前一刻山崩地裂,人生就此动摇,可此刻需要你出面,你依旧得外表光鲜地站在灯下笑脸迎人。所有辛酸,所有痛楚,全部得打碎牙齿和血吞。权利与财势赋予的责任重如泰山,一人戴一个面具,若时运不衰,就得永远戴下去。
这个shijie,得失永远平衡,谁也不用妒忌旁人。
走前唐忱上楼来找到她,憋了好长一口气,才说:“对不起……”尾音拖得长长的,似有不甘心。
文清决定不理他,埋头睡去。
次rì,文清醒得很早,因为姐姐跑来叫她起床:“快随我来,我发现了一件事。”
文湘将妹妹从床上拖下来,一直带到书房。两个孩子轻手轻脚走进去。
仿佛有什么不对劲。
文湘一指,文清立刻发现,书房落地窗的玻璃给什么东西砸了一个大洞。
许久以后文清回想起来,已经可以利落地分析出当时情况。若是捣蛋的客人,如唐忱,从外面丢了东西进来,玻璃碎片定会落一地。可当时屋内并没有碎片,可见是屋内的人扔的东西。再一回想,那天下午,家中花王就从窗外的花圃里找到一个黄铜纸镇,交了回来。
前一天晚上,屋内必定发生过激烈争吵,父亲——一定是父亲,一气之下拿起纸镇就砸了出去。
文清后来对文湘说:“真是不敢想象,他居然会为了留住一个不是亲生的女儿而和恩人吵架。”
文湘一份文件接一份文件地签署着,回妹妹道:“所以我总对自己说,不论我遭遇到多么可怕的事,我毕竟是被父母深爱着的。所以我一定不能放弃自己,这才是报答了他们。”
文清酸涩道:“想不到母亲这样冷静理智的人,也曾为aiqing牺牲至此。”
“她再冷静理智,也是一个女人。”
妹妹苦涩地笑,“一个可爱的苯女人。”
文清一直怀疑文湘其实在那个早上,就已经看出了个所以然了。
那天早上在餐桌旁,谁都没有多说话,费氏伉俪并没有交谈。文湘忽然开口问:“后天,一辉他们要出海,我可以一起去吗?”
父亲放下叉子,温柔道:“可以,但要注意安全。”
文清一直盯着父亲看,可父亲并没有提到她。她不是个多话的孩子,没有开口问。父亲转过来对她说:“妹妹还有伤,出海我不放心。”
母亲眼睛一直盯着眼前的盘子,始终一言不发,有很重的心事。两个孩子都看出来了,更不要说大人。费则诚看妻子一眼,说:“明天晚上公司年终的宴会上,赵氏的庄董事长和他新婚妻子要来。”
费夫人才回过神,丢下叉子,道:“我去看看。”答非所问。
父母之间的那个心结,直到多年后才得以解开。那是一段又长又悲的故事。
而文湘也未能同蒋氏tianqi出成海。人在商场,风云巨变也只是转瞬的事,作为孩子,zì yóu身不由己地承受下来。
事情自父母出席公司在年终招待职员的宴会回来后得到的。文湘同父母一同去了,一回来,立刻悄悄尾随父母,站在书房门口偷听。文清见状,虽不懂,也不肯落后,跟着跑了过去。
费则诚语气沉重:“真想不到,前天一家大小还喜气洋洋地来给文湘过生,我正打算约个时间和他谈谈在佳利上柜的事……没想到……”
孙长宁的语气里也满是担忧:“听说在公海上被公安截住的时候,还发生了武装冲突。他身边那个王有志当场就给打死了。”
“老蒋糊涂啊。我早提醒过他最近查得严,要他收敛点。他偏偏不听,犯这种低级错误。”
孙长宁叹气:“我们还是先想想自己吧,该销毁的就趁早。”
“放心,学优已经在处理了。你手下的生意也注意点,虽然是干净的,但难免被人抓住什么。”
“老蒋这一交栽得有点蹊跷。”孙长宁迷惑,“这样做事真不像他。”
“你提醒我了。”费则诚说,“蒋家的教训在前,我这次真的考虑收手了。”
“那些弟兄……”
“开一两个娱乐城,总安置得了的。”
孙长宁长叹一口气,“可怜了蒋家的两个孩子了。”
费则诚疑惑,“两个?不是只有一个蒋一辉吗?”
“蒋正风有个姐姐,嫁得不好,后来病死了,男方不负责任不肯养孩子,蒋正风就把外甥带回自己家来抚养。”
“是吗?“父亲淡淡说。
费氏姐妹就再也没见过蒋氏tianqi。姐姐告诉妹妹,这叫落难,蒋家现在没钱了,父亲不许孩子同他们来往。社会就是这么现实,避平阳虎如大麻风。
不久,蒋太太带着孩子去了新加坡娘家,蒋家大宅宣布对外拍卖。
孙长宁说:“蒋太太娘家只是普通的书香门第,不然这时候若有岳家救济,蒋正风也不会落得这样狼狈。”
她丈夫说:“其实他们也不用愁生活的。”
“过惯了奢华的生活,现在突然被打回成小平民,还背负着父亲的罪名。”
“没有过不去的槛。”
费氏夫妇很快就不再谈论蒋家了。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一刻,又有多少达官贵人收拾细软离开了白玉为堂金做马的府邸,就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小文清时常想起那个白衣少年,想起他宛如玉雕琢出来的容颜,想起他拉小提琴时的优雅。但她也zhidao她再也见不到他了,因为他们家没钱了。她又想,姐姐说过等她们长大了,父亲就会给她们很多很多钱。她可以把这些钱存起来给他啊。如果能zaijian到他,和他做朋友,自己没有钱买好多的冰淇淋,也并不要紧。
费家其实也并没有清静下来。或者,看在小小的文清眼里,家中的巨变更甚于蒋家的衰败。
唐忱那天回家后,好生挨了一顿教训,终生难忘。照理说本该就次怨恨文清的,可他看到一连一个星期,文清头上都缠着白纱布,所有不满都自己消化掉了。他提醒自己,他是男人,保护妇孺是己任,父亲也教导他,千万不可让女孩子流泪。
他后来叫母亲照着样子买了新的珠花,悄悄塞在文清的枕头底下,结果给文清从窗户里丢了出来,火辣辣的脾气。他不罢休,从楼下拣回来,一次次放回去,也给一次次给丢下来。
等到这个珠花给丢得差不多烂完了的时候,文清也拆了纱布了。于是干脆打开窗户,对站在楼下的唐忱喊:“我才不要你的东西!”
唐忱笑,“那我不给你送东西好了,你下来,我带你出去玩。”
文清心动了。因为受伤,她这半个月都给禁足,哪里也不能去,早就闷坏了。她本有野xìng子,怎么关得住?
唐忱还在楼下喊:“文清,快下来!”
快下来!走出来!站起来!走下去!
文清这辈子都记得唐忱对她说的这几句话。
文清终于在唐忱的帮助下——其实是由他背着,从二楼滑到一楼,顺利溜了出来。这一次出逃,为rì后文清的多次翘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忱带着文清去逛了小吃街。两家大人是从来不准孩子到这种地方吃东西的,唐忱也是上学后跟是同学偷跑来过。文清是第一次zhidao原来外面有那么多新奇的小吃,烤兔子倒着挂成一排,牛肉串在火上滋滋响,鱿鱼一炸就缩小好多。
那天文清玩到傍晚才回来,手里还抓着唐忱买给她的一把羊肉串,吃得津津有味。
唐忱送她回了家后便走了,她一边意犹未尽地舔着手指头,一边跑进房子里。
那个男子正好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文清面对面。
文清后来一直记得非常清晰。那男子同父亲一个年纪,容貌英俊,身形修长,穿着深灰sè西装,温文儒雅,和蔼亲切。
他对着文清温笑:“你是文清是不是?你今年五岁。”
文清呆呆看着他。
那人说:“我是你爸爸妈妈的朋友,今天是来看你姐姐的。”
真奇怪,为什么要看文湘?
说话间,孙长宁从学校接女儿回来了。她埋着头走进客厅,一抬头就看到那个男子,脸sè瞬间变得纸一样白。文湘又惊又怕,下意识地躲到母亲身后。
男子的眼睛里满满是温柔,注视着文湘,却对孙长宁说:“我……今天飞机回美国,来同你们道别的。”
孙长宁一听这话,松了一口气,又立刻觉得表现得太直白,声音打着颤说:“这就要走了?不如……不如今天在我们这吃顿饭吧?则诚很快就下班了,你们俩也很久没聚了。”
男子的笑容变得苦涩:“不用了。我今天去过公司,和他已经聊过了,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我这次来你们家里,只是……想见一见……孩子……”
孙长宁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咬着牙,把文湘从身后拉了出来,往前推了一把:“别那么没礼貌,快叫叔叔!”
文湘到底只有十岁大,给这怪异气氛吓住了,结结巴巴地叫了一声:“叔……叔……叔叔好。”
男子的笑容在这声“叔叔”中变得凄凉且哀伤。他蹲了下来,对着文湘微笑:“文湘你好,你长得像你妈妈一样漂亮,将来一定是一名大美女。你要好好学习,做一个让你爸爸自豪的女儿哦。”
文湘黑嗔嗔的眼睛盯着他,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孙长宁的眼睛里已经积蓄满了泪水,仿佛一不小心就会涌出来。她说:“你……别这样。其实当初都是我不好。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她。她就是我的命。”
文清站得离他们有些远,但还是把这句话听清了。同时,母亲一手把姐姐揽在怀里,紧紧抱住,像抱着什么稀世珍宝。
妈妈从没有为她如此激动过,也从未这样拥抱过她。父母心中最重视的孩子一直是文湘,他们的目光和拥抱也都一直只属于文湘。
文清的眼睛也热热的,不过只有五岁的她并不zhidao这个感情到底是什么。
那个男子慢慢站了起来,原本挺拔的身形似乎就在那短暂的时间里佝偻了许多。他伸出手想摸摸文湘的头发,可是她惊慌地往后躲,他的手无力地垂了下来。
“我该走了。”
孙长宁的脸上已经湿了:“我叫司机送你。”
“不用麻烦,出租车就等在路口。”
男子拿起大衣,缓缓走了出去。
文清从窗口看到了那个男子离开了费园。黄昏时分,那个孤寂的身影走在盛开着青心菊的小路上,是一幅画。
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过这天发生的事。连文湘也不和妹妹说。文清向来不多话,也从不问。大人不zhidao她zhidao,她也不zhidao自己zhidao点什么。
这段记忆沉淀了很多年,才慢慢浮出水面,激起一阵波澜。
而费家的生活依旧得继续。
父母还是那么忙碌,姐姐越发地聪敏伶俐,妹妹依旧顽劣寡言。岁月的光yīn一次次在书房那块波西米亚风格的地毯上投下窗棂的yīn影,一次次敲响那架史坦威钢琴的琴弦。蒋家tianqi再也没有信息,而父亲的生意却越来越大。
或是宴会,或是派对,费园并不寂寞。而那欢聚后的寂寥却一直淡淡地萦绕在每个费家人的身上。
文清常在黄昏依着窗棂俯视花园,那条小路上依旧年年chūn天盛开满青心菊,可始终少了一个人,无法成景。
童年,是最xiongdi过去的一段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