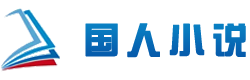天高云淡,大漠孤烟直。
一行鸿雁斜飞。
贺锦心抬眼直至鸿雁消失在天尽头,纵有弯弓射雕之心,却苦于手无寸铁,只能握紧空空的粉拳,恨恨地咬了咬牙。
此刻若能射下一只大雁来,多少给她的父亲带来哪怕最微弱的一点生的希望。
然而她只能舔一舔干裂的嘴唇,将最后一滴水滴在父亲的唇间。
两个官差紧盯着锦心手中的羊皮水袋,但没有动,因为他们都很清楚,再也倒不出任何一滴水了。
“可怜哪,堂堂京都府尹,曾是何等八面威风,一朝落马到了这步田地,还不如往常市井人家一饮一食来得悠闲自在。”
“老哥此话说差了,这卖国背主之人有啥好可怜的?谁叫他勾结契丹人对我大周图谋不轨?一切都是咎由自取罢了,圣上心慈宽仁,没将他满门抄斩,只判了个流充边塞,也算是他祖宗辈给他留了厚德吧。”
两名差官一老一壮,斜倚着枯树根,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间或拿眼斜觑一下几步开外的贺锦心父女俩。
那壮年差官忽地将眉目一转,压低了嗓音说道:“哎老哥你说,这一大家子自开路以来,一路上死了个七七八八的,可这老东西却忒是命硬,要死不死的竟然拖到今日,还有这小娘们……”
声音越来越低,逐渐变成了耳语,两名差官交头接耳不时发出一两声干笑,又很快被风沙带着传入贺锦心的耳朵里,令贺锦心的心头不禁一凛,警觉地抱紧了怀中包袱。
这时父亲贺钰捂着胸口发出一连串的咳嗽声,一丝暗红的鲜血从嘴角缓缓淌出。
“父亲……”贺锦心呼唤着,忙用衣袖为父亲擦试。
贺钰轻轻摇了摇头,沙漠正午的阳光打着一轮又一轮的光圈直射在他的脸上,愈显得苍白老态,生命已剩下最后的一缕游丝。
两个月之前,贺钰还是大周京城汴梁府尹。
都说京城的府尹最是难当,而贺钰生性忠厚耿直、嫉恶如仇,且由于他刚正不阿,为官清正,在京城之中倒也赢得赫赫官声,朝中大员、皇亲贵戚们见到他时都客客气气礼仪有加。
当然,得罪人的事也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清河潮汛急危,朝廷年年拨款整修河道年年失修,洪水泛滥成灾,民不聊生。
而贪墨大批治河钱款的正是当朝太傅杜彦。
铁面御史沈潭历时半载,掌握了大量证据,联合贺钰共同上奏弹劾杜彦,却不料最重要的证物在送往皇宫的途中被劫,证物再无处查起,原本铁板钉钉的案情急转直下。
翌日,那盗贼被人灭了口,横尸街头。
巡捕从盗贼身上搜出的,竟然是一份沈潭贺钰与北汉刘崇的使臣相互往来的手书,手书的内容为北汉意欲联合契丹人攻打大周,沈潭贺钰则做为内应。
沈潭贺钰弹劾杜彦不成,反而坐实了通敌背主的罪名,连同贪墨治河款的罪名通通倒扣在了他们身上。
白纸黑墨,字字都是沈潭亲手所书,二人百口莫辩。
“清河不清,浊流害民,奸人不除,愧对黎民。”
沈潭悲恨交加,当朝触柱而亡。
贺钰则落得个削官夺职,充军边关、抄家没产的下场。
除了大小姐贺锦衣正好在外拜师研习琴艺而侥幸逃脱之外,一家子老老小小十多人口全都象牲畜一般被驱使着往关外赶。
一家老小哪里受过如此磨难?刚刚出得关来,便一个个地倒下,三位夫人相继去世。
小妹贺锦颜眼看着也快死了,两官差一合计,趁着锦颜还未断气,竟然悄悄将她卖与一位到关外贩皮货的徽商,锦心发觉追出去已不见小妹踪影。
原本十多人口,只剩下贺钰与次女锦心父女俩苟延残喘,强撑勉行。
一路风餐露宿的艰辛自不必说,在两个官差紧催慢赶大呼小喝中艰难跋涉,好不容易捱到了边城,眼看着离役营不远了,越过沙海就算是到得地方,贺钰却是一病不起。
锦心日夜照看父亲,也是精疲力竭。
“官差大哥,我父亲病得不轻,实在不能继续行走了。况这里已是边城,离役营也是不远了,就让我父亲歇两日吧?”
“不行,得快些去役营交割了,我俩好赶回京城,家中老小还等着一起过年。你当自己还是府尹千金大小姐呢?在这指手划脚?”
“我说千金大小姐呀,也不是我俩不通情理,你看这天儿指不定哪日就该有风暴,到时候沙海过不去,岂不又耽搁了许多时日?”
年长的一位官差看着一老一小,有些过意不去,说些道理给锦心,总之还是逼着他们赶路。
这两位官差掐着指头算着回京过年的时日,一日都不肯迁延,逼着锦心搀扶着老父,哆哆嗦嗦地进了沙漠,却不想这一脚便踏进了鬼门关半步。
他们刚入沙海就刮起了暴风,退出来已来不及,渐渐地迷了方向,原本五、六日的路程,在沙海里兜兜转转逡巡了十多日还没有走出去,而粮食和水也已断绝。
贺钰一个书呆子哪里受过这般苦楚,熬了几日眼看就要熬不住了。
“父亲,这一大家子都没了,小妹被不良差官卖了,大姐也不知流落何处,您可不能再丢下女儿一个人啊。”
锦心守着父亲悲鸣,望断南飞雁,只恨自己空有一身三脚猫的武艺却没法弯弓引射。
“锦心我儿,为父害苦你了。”
贺钰满是皱纹的眼角落下一滴老泪,望着女儿悲伤的脸,想抬手抚摸,终究无力地垂下,气息奄奄。
贺家无子,三位夫人各生一个女儿,大小姐锦衣天姿国色,擅长琴艺,三小姐锦颜年纪尚小,乖巧可人,最会卖乖,在父亲身旁修习诗文。
唯有二小姐锦心最不安分,女儿家家的偏喜刑律断案之事,常常假扮府中捕快跟随父亲身边,顺便也跟着府中捕快们学些拳脚剑式。
捕快们都只当她是玩笑,唯有捕头桓靖大哥尚肯认真教她一招半式的。
只是她学起来四不象,桓靖大哥笑她的掌式为“绵绵掌”,空有架式,而没有半点杀伤力。
贺钰每日从府堂回来便与两个女儿吟诗弹琴作乐,再看看二女儿耍几招三脚猫的功夫,倒也其乐融融,颐养天年。
却不想有朝一日突然遭此飞来横祸,落得个戚戚然家破人亡。
“想我贺家世代书香门庭,终是断送于我这无用之身。若不是证物被贼人所劫,莫名被指勾结乱贼,又怎会落得如此凄惨境地?杜彦奸贼犯科,害我忠良,此恨难消。皇天不公、不公哪。”
“父亲且再坚持片刻,穿过这片沙海就快到役营了。”
贺锦心宽慰父亲也是宽慰自己,而茫茫沙海哪里是尽头?
“证物、证物……”父亲的手渐渐地垂下,而他那没有血色的双唇歙动着,只重复这两个字。
贺锦心眼看着父亲气若游丝,于悲苦之间抬起头来,却发现两个官差在一旁鬼鬼祟祟地小声嘀咕,眼神时不时地往贺钰身上瞟。
不禁心头一凛:这两个恶差莫非要起歹意?
果然两个官差各持一把钢刀一前一后向贺钰与锦心包抄了过来。
“你们要干什么?”
“我说,这府尹老爷就快咽气了,而我们缺水少粮的,不如就成全了我们,否则谁也别想走出这个鬼沙城。”
“休得无礼。”
贺锦心心中惊恐,两位恶差竟然想要杀人喝血吃肉,锦心又怎肯让他们伤父亲分毫?
锦心迅速起身,双掌呈剪刀之势,守着父亲是寸步不让,与两个恶差对峙着,生死关头,双方都红了眼,一场恶斗即将爆发。
贺锦心已经多日滴水未沾,饿得前心贴后背,实力悬殊可想而知。
但她毫不退缩,有如沙漠中一只小豹,为了保住父亲,就算只会几招三脚猫的功夫也无论如何要与两位恶差拚个你死我活。
她是相当虚弱的,但苍白的脸庞上满满的却是无比的倔强,一边护住父亲,一边提着丹田努力支撑着自己决不倒下。
她机警地将眼睛瞟向那两把步步逼近的钢刀,在阳光的直射之下倒映出两张丑陋邪恶的脸庞令她觉得有些恶心,同时咬了咬嘴唇暗暗下了夺刀杀人的决心。
正相持间,忽地远处一阵马蹄声急,夹杂着嘈杂的呼哨声,同时箭翎呼啸而至,一支正中一名官差的心脏,一支射穿另一名官差的喉咙。
两人尚且站了片刻才扑身向前倒在沙海之中,目光幽幽正与贺钰相对。
“锦心我儿……”
贺钰叫了一声,瞪圆了双目,叫声被剧烈的咳嗽声打断。
锦心挂念父亲安危,急忙回过身去,却没有防备身后一个马鞭飞来给她沉重的一击,头重脚轻,堪堪栽倒在父亲面前。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已被一个奔马而来的人提了起来倒挂在马背上。
“我的父亲,求求你们救救我的父亲。”
贺锦心艰难抬头,哭求救命,但那个人只是拍马在贺钰的身旁绕了一圈,并未有停留的意思。
贺锦心努力地伸手,却够不到父亲,只见父亲双目紧紧望着她,渐渐失去了光泽,张着嘴,叫不出声。
那人摇了摇头,打了个呼哨,策马而去。
“父亲,我的父亲啊,求求你们救……”
贺锦心的话音未落,群马已经飞奔,倒悬着的脸冲着满地黄沙,只看见父亲的身躯被飞扬的沙海掩埋,渐渐地隐没在视线之外。
贺锦心横趴在马背上被颠得七荤八素的,更兼泪眼模糊黄沙扑面看不清路,一路上只听得马蹄声碎、铃儿叮当,自己象货物一般被驮着“运”到了一个兵营里。
又一个呼哨过后,她被人“卸”了下来,一提一拽又扔进了马厩。
马厩的杂草堆里躺着一个人,用个破毡帽盖着脸,听到有人来,摘下帽子抬眼瞧了瞧,又盖上帽子呼呼地睡。
“请问……”
贺锦心从地上爬起,虽然狼狈不堪,但还是保持着汉人女子谦谦的礼仪,面对那个人施了一礼,问道:“这位兄台,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那人没有回答。
贺锦心只得又问了一句,那人翻了个身继续睡,还是没有回答。
贺锦心终于怒从心头起,上前一把掀开破毡帽,冲着那人耳边高声问了第三遍:“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那个人一脸的不耐烦,回了一声:“马厩。”
贺锦心哭笑不得,她又不瞎不傻,怎会不知道这里是马厩?问题是哪里的马厩嘛!
然而此刻的贺锦心已不再关心这个问题了,因为她的注意力被放置在一旁的一个半开的包袱所吸引,白花花的干馍馍半隐半现。
贺锦心咽了一口唾沫,问了声:“我可以吃吗?”而她的手早就已经伸出去一把抓住馍馍就往嘴里塞。
馍馍又干又冷,噎得她两眼冒泪花,左右一扫眼,见着一个羊皮囊打开就“咕嘟嘟”地灌个饱,早已将官家大小姐的诗书礼仪抛诸九霄云外去了。
而那人始终躺在干草垫上,未曾正眼瞧过贺锦心一眼。
贺锦心打了个饱嗝,这才心满意足地顺了顺气,又将注意力重新回到“这是哪里的马厩”这个重要问题上来。
那个人被贺锦心连连逼问得被迫坐了起来,又是摇头又是叹气:“睡个觉都不安稳。好吧,我回答你,这里是契丹人的前营,距离大周的营地不远,但是要穿过大半个沙漠,没有充足的准备是回不去的。”
“你怎么知道我是大周人?”
贺锦心的话一出口知道自己问得有多白痴了,一身大周人打扮还不够明显?
果然那人眉头一皱,将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一番,嘲讽和不屑都写在他的脸上。
这时贺锦心也才认真地看了看面前这个马夫,脸上轮廓明朗,线条分明,尤其是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虽然他尽量装做睡眼惺忪的样子,但还是掩饰不住从里到外透出的那一股英气,竟与这脏臭的马厩有着天壤之别,令贺锦心暗暗称奇。
“你也是被抓来的?”
“废话。”
当然是废话啦。
一个汉人打扮的人,睡在辽人的马厩里,不是俘虏还是什么?
贺锦心哑口无言,发觉自己在这个人面前真的是处处显得白痴一般,尽是呆萌出丑,难道这大漠的风沙把往日那般精明聪慧的机灵劲都刮没啦?
马夫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干草,将角落里的一个木桶朝着贺锦心踢了过去,说了声:“干活去。”
贺锦心一瞧,木桶脏兮兮的,放着一把黑乎乎的大刷子,一股难闻的骚味直往鼻孔里钻,不禁退缩了一下,一脸茫然,问:“干、干什么活?”
“你刷马,我喂草。”
“怎、怎么刷马?”
马夫显然被贺锦心打败了,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很无奈地说道:“我来刷马好吧?喂草你会不会?……什么,给马喂草也不会?那你到底会什么?”
那目光凛凛,一双冰刀般的眼神似乎将贺锦心整个人剥得体无完肤一般,令贺锦心不禁心头一震。
“我、我会杀人。”
贺锦心防备心理立即炸毛,将眉心一挑,冷冷看了一眼马夫,双掌已不自觉地呈现剪刀式防御之势,随时准备出掌。
马夫亦冷眼看了看面前这个又脏又丑的丫头,摇了摇头走出了马厩,无语向苍天。
想了想,狠狠地抓了一把干草,默默地喂起马来。
而他的眼望向天空,正好一行鸿雁斜斜地飞过。
贺锦心提着木桶走到了他的身边。
“对不起,这位兄台,我实是不知该怎么做,还请兄台赐教好吗?”
那人依旧是冷冷地看了她一眼,稍稍做了个示范动作。
贺锦心是个聪明的女孩,一看就明白了,接过刷子认真地给马刷着鬃毛。
她虽然是庶出,但无论如何也是出身官宦人家,养在深闺里,刷马喂草这样的事情她只是没有见过而已,一旦上手,就做得十分到位,那个马夫看了半晌也没能挑出刺来。
只是,刷着刷着,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掉下来,落在木桶里,叭嗒叭嗒地响。
“怎么?”
贺锦心抽泣着:“我的父亲一个人留在沙漠里。”
马夫沉默了,这种情况他十分清楚,一个老人留在沙漠里,根本就没有活下来的希望。
免不了同情地看了看小姑娘,默默地拿过她手上的刷子,刷起了另一只马的鬃毛。
贺锦心也就顺手拿起一把干草去喂马,两人无言倒也配合得十分默契。
“草料没有了。”贺锦心有些为难地对马夫说道,小心翼翼地怕马夫又嫌弃她。
马夫这回倒没说什么,走到一边去铡起草来,贺锦心蹲在一旁看得仔细,不一会儿就已经学会。
但那铡刀实在太沉重,马夫突然地怜香惜玉起来,没让她上手,只说:“一边儿呆着。”
贺锦心觉得这个马夫似与其他男子不同,尽管破毡帽遮了半张脸,眉眼间却总有一股豪放之气掩藏不住。
依旧蹲在他的身旁,看铡刀在他的手中上下起落,干草纷纷落地,一如自己在家中后园荷池边伴着姐姐锦衣的琴曲翩翩起舞时柳絮纷飞的样子,一时间竟有些看痴了。
夜幕降临的时候,贺锦心未免发起愁来,因为马厩就那么点大,要让她与一个陌生的男子同处一室过夜,这怎么能接受?
马夫可管不了那么多,见她不肯进马厩也不会去请她。
辽营的篝火通明,不时地传来远处羌笛断断续续的呜鸣。
“我寄愁心与明月,何日送至京城西?”
贺锦心斜倚在马厩外面,一边想着遗留在沙漠里的父亲,一边垂泪,更兼思念下落不明的大姐锦衣以及被卖了的小妹锦颜,不禁悲从中来,抽泣不止。
马夫原本呼噜声一阵阵的,听到她的抽泣声,停止装出来的呼噜声,走到了她的身边,静静地坐着仰望夜空。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马夫望月轻吟,手中一把干草却扯得粉碎。
贺锦心独坐于马厩外对着苍茫黄沙正自感自伤,忽地闻听那马夫对月吟出一句诗文来,
心内不免十分惊异,欲看这马夫时,却又将破毡帽压得更低些,教人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只见马夫嘴角轻轻上扬,吟罢了月光,慢条斯理说了一句:“明天,是大辽龙珠太子大婚之日。”
贺锦心梨花带雨,没好气地问:“龙珠太子大婚跟我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马夫的回答直截了当。
“龙珠太子治军十分严明,他的士兵不敢任意妄为,尤其在女人方面有特别约束。否则,你以为辽兵怎么会把个大姑娘扔马厩里而没有带到营帐里去?”
马夫说罢斜睨了贺锦心一眼。
贺锦心愣了一下,确实没有想到过这一点,虽然在沙漠里摸爬滚打风吹日晒的早已狼狈不堪,但仍不失一位官家女子的高贵气度,辽兵也不是瞎的呀。
“那,龙珠太子大婚,会怎样?”
贺锦心有点紧张地吞了一口唾沫。
“龙珠太子大婚,辽人举国上下欢庆呀,对士兵的约束自然也放松了,只要不对有主的妇人下手就不算违犯军纪,这里是辽军前营,除了你之外没有多余的女子……”
马夫斜觑着贺锦心,笑了笑,眼神中满满都是同情,好像贺锦心马上就要大祸临头。
贺锦心跳了起来,慌张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外面是漆黑一片,天空中繁星点点,而她却是无路可逃。
就算从这里逃出去,也逃不过沙海,最终的结果也象父亲那般被无尽黄沙吞没。
可是,若要被那些辽兵带到营帐里,还不如就此了结,免得受那百般屈辱。
望着辽人营帐里透出的灯火,打了个寒颤,竟然觉得这个马厩是最安全的地方,一个激灵,钻进了马厩,躲在马夫睡觉的干草堆里。
“喂,这是我的地盘,我的草垫。”
马夫不客气地驱逐贺锦心,但贺锦心铁了心不肯出去,将草垫当被子捂着自己的身体,任马夫怎么拉扯都不肯松手。
二人拉扯了一阵子,马夫彻底放弃争夺,默默地躺在一旁,闭眼不理贺锦心。
没了草垫,他只能躺在地上,冰寒刺骨,眉间不觉得地微微蹙紧。
马厩里暂时安静得只有马夫的呼噜声。
而贺锦心却是辗转难眠。
明日是龙珠太子大婚,自己也将厄运当头,如何能睡得下?两名恶官差尚还能与之一拚,而辽兵无数,孤身一人怎么对付?
马夫睡在地上,冷得蜷缩成一团,而他的腰间挂着的一把马刀映入了贺锦心的眼帘。
她试着探手去解,却被抓了个正着。
“要干什么?”贺锦心越是挣扎,那人的手抓得更牢。
“给我。”贺锦心放弃挣扎,苦苦哀求。
而那人却无情地甩开了她的手,护紧了马刀,冷声道:“凭什么?”
贺锦心的泪涌了上来,说不出任何理由。她只想用这把刀,来应对明日的危难,但是,人家凭什么给你?
马夫见贺锦心又是泪流满面,动了恻隐之心,摇了摇头,却依旧护住马刀不给,侧身将马刀压在下面,贺锦心再想抢也没有机会了。
“同是大周之人,何苦这般无情?想你家中也有母亲姐妹,怎能看得我明日受胡人凌辱?借你一把马刀,却是这般小气。”
贺锦心抱着干草垫蜷在一角,嘴里碎碎念叨,马夫将手捂紧了双耳,不听。过了一会儿,轻轻的鼾声又起,贺锦心恨极,又奈何他不得。
长夜凄凄,贺锦心盼天明又怕天明,龙珠太子在她心中愈加显得狰狞可恨。
忽地想起,之前听马夫说过,有主的妇人可免遭受辱?
贺锦心的眼中闪过了一丝生存的希望,捧了干草垫,推了推马夫,说道:“喂,你娶我可好?”
心想,嫁个马夫总强过被契丹人凌辱。
马夫从睡梦中跳了起来,借着朗照着马厩的月亮,看她满脸尘灰、泪痕斑驳,头发凌乱还沾着几许干草,从头到脚足足看了她两三遍,从他那弧度十分优美的双唇间吐露出两个冰寒的字来:“休想。”
贺锦心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主动开口下嫁马夫会被如此断然地拒绝,颜面尽失,惊疑与羞愧交加,止不住又是泪流满面,哽咽抽泣。
可恶那个马夫还不罢休,一把扯了她身上的干草垫,还冷声冷气地说:“你这女子怎地如此聒噪?一晚上的哭个不休,还让不让人睡啦?”
贺锦心索性放声大哭,气得马夫连个呼噜声都打不匀。
“唉,你就是泪罐子,泪沫儿。”
只听说糖罐子、醋罐子的,却从没听过什么泪罐子,而今贺锦心真是泪罐子打破泪沫儿横飞,抽抽嗒嗒哭了一阵子,自觉无趣,转向墙角咬着袖子想着自己的伤心事。
父亲那张苍老的脸庞总在眼前飘飘忽忽地,眼见着父亲羸弱的身躯被飞扬的沙海掩埋时,那种锥心的疼痛令她一次次深深地心悸,忍不住捂住了心口半晌才返过一口气来。
贺锦心泪眼模糊中将“杜彦”这个名字牢牢记在心上。
一切的缘由皆因当朝太傅杜彦而起,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证他栽赃陷害,更没有任何线索可以为自己的父亲申冤平反。
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从贺钰被指控“叛国通敌”到全家流放只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贺锦心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已经随同一家老小被关进大牢继而被驱使流徙。
一向拖沓的朝庭在这件事情上却一反常态,可谓前所未有的神速,看起来更象是一场早就策划好了的阴谋。
若有幸留下一命回得京城,必得找上杜彦,将那份所谓的“通敌叛国”的手书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只可惜现如今自己身陷番营,前景堪忧,摆在眼前的就是明日龙珠太子大婚庆典,到时候失控的辽兵可就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她了。
想到这里,贺锦心咬了咬牙,恨声道:“大不了与胡人拚个你死我活罢了,就算只剩得一缕幽魄也必得回到汴京,查明真相,雪冤报仇。”
“就凭你?怕是连魂魄也回不得京师,通敌叛国之罪,人人得而诛之。”
呼噜声攸忽停了下来,耳边传来马夫那冰凉刺耳的冷语,如芒刺一般刺疼贺锦心。
疼痛之中却又猛然惊疑:“他一个囿困于辽营的马夫,如何知道这所谓的‘通敌叛国’之事?”
马夫似乎一眼看穿了贺锦心的疑虑,缓缓说道:“沈贺一案震惊朝野,沈潭已当朝伏诛,贺氏一族流徙充军。而这大漠黄沙之中,除了情非得已又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官家大小姐出没?”
贺锦心哑口无言。
是啊,如若不是家门突遭巨变,她又怎么可能独自流落这边远黄沙之中?
“贺家三位小姐名闻天下,尤其是二小姐聪慧伶俐善断奇案,就连当朝杜太傅也忍不住争着下聘以将贺家二小姐娶进门为荣。贺钰看似清高,却也免不得将自家女儿当做攀龙附凤之筹码,想来会通敌卖国之人,样样精于算计,这样做也是情理之中吧?只可惜,双方都打错了算盘。”
贺锦心闻言,一股血气上涌,差点晕厥过去。
咬紧了牙关,两眼冒着怒光,哆嗦着恨恨然迸出话来:“我父亲从未曾做过通敌卖国、背主求荣之事!再说,当初与杜家结亲,并非我父亲攀龙附凤,实是看上了杜家二公子人品才华,这才受了杜家之聘。其情其理,你个番间小厮,又怎能知晓?”
贺锦心说着,瞪视了那“番间小厮”两眼,跺跺脚,扭身走出了马厩。
“饿死冻死,也决然不与你个恶厮同一屋檐下。”
正当贺锦心独自坐在马厩门边生着闷气的时候,突然马厩的栅栏被人踢开,一群辽兵嬉笑着拥了进来。
为首的一位似军曹模样的人手中擎着酒囊,歪七倒八一路吆喝着径直朝锦心而来,满嘴喷着酒气,围着锦心满口污言秽语。
贺锦心认得,正是沙漠之中杀了官差将她掳至辽营的那个人。
“大周女子,来来来,今夜良辰美景,陪爷几个喝盏交杯酒……”
一边说着,一边伸出一只手来欲往锦心脸上摸,被锦心一巴掌打开了,众兵顿时高声起哄笑闹起来。
那军曹也不恼也不怒,恬着笑脸继续伸手挑逗锦心。
贺锦心被激怒,一边往后退一边摆开双掌阵势祭出她独有的“绵绵掌”打在军曹肩上,那军曹却兀自纹丝不动。
军曹反而被锦心无力的反抗挑动了兴奋的神经,索性将酒囊子往边上一甩,一伏身便将贺锦心扛在肩上,打了个呼哨:“走喽,陪爷一起洞房花烛去。”
“放我下来,你这番贼。”
锦心被倒挂在肩上,着急忙慌地又是喊又是叫,拚命踢腾双足,“绵绵掌”雨点般捶打着军曹,无奈那招式煞是无力,果真如桓靖大哥取笑的那般“柔软若绵”,众兵丁嬉笑更欢,并不理会贺锦心无谓的反抗。
“放下她,此女有主。”
耳边传来一成不变的冷漠之声,贺锦心努力地抬起眼来,朝马厩望去,那马夫站在马厩门前,月光如水般倾洒在他的身上,有如环罩一轮银光,破毡帽下却是一张面无表情的脸庞。
辽兵军曹愣了一下,眼巴巴望着马夫:“有主?主在何处?”
破毡帽稍稍向上一抬,朗声道:“正是在下。”
“胡说八道,这女子我午后才从沙漠中弄了来,暂且存放在此处,你又于何时成了她夫主?”
马夫不慌不忙,沉着应对:“女子午后来此,傍晚与我定的亲,明日借着龙珠太子大婚沾些喜气一同成婚,正是天赐良缘,有何不可?”
军曹被扫了兴,尚且不肯罢休,指着马夫怒吼:“好你个小乞儿,那日若不是我见你一个人流落沙海,心生可怜把你带回来养马给了你口粮草活命,你早就不知身骨埋于何处了,今儿倒有能耐跟爷抢起女人来?”
马夫将破毡帽按了按,遮住半张脸,但对于辽军的挑衅却是应答得一点也不含糊:“承蒙贵人相救,我感激不尽。只是我来此地虽不多时日,却也知晓龙珠太子治军甚是严谨,并有明令一应兵将不得叨扰民间夫妻,今夜你等若是执意闹将起来,恐怕惊扰了太子,到时不知几位是受着军棍呢还是马鞭?”
众兵闻听此言,立马噤声。
龙珠太子纪律严明,喝酒闹事违抗军令非同小可,况龙珠太子就驻扎在前营,惊动大驾谁都吃罪不起,因此个个悄声开溜。
那军曹没了底气,肩上一松,贺锦心便“咚”地一声跌落在地上。
军曹怒气冲冲出了马厩,却犹自不甘心地回头恨骂:“你们等着,有你们好果子吃的时候。”
马夫看都不看一眼地上的贺锦心,便转身回到马厩里,依旧将破毡帽盖在脸上睡觉。
贺锦心无力地坐在地上,半晌没有起身,望着静悄悄的马厩,虽然有心对那马夫道声谢,却又傲娇矜持不肯轻易开口。
北地的夜霜寒如冰,那马厩虽然不是人住的地儿,但总还是遮寒挡风的所在,且多少有个干草垫可以抵挡这塞外的似铁的风刀。
贺锦心再如何骄矜也抵挡不住寒夜漫漫,想了想,最终还是不管不顾一头扎进了马厩里去避寒。
此时此刻,贺锦心突然发现,那破毡帽遮掩下半露着的脸庞似乎没有之前那么可恶,就连那轻轻发出的鼻息声也带着稍许令人心跳的魅惑。
“这小厮看着似有些可恶,危难时刻倒肯相救于我,只是这不明不白地忽然就与他成了夫妻,他日若是地下见了父亲却是如何禀告?”
静静地望着已经熟睡着的人儿,却是有些痴了,不禁脸上热了一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