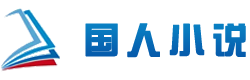马跃与眉儿一唱一和地将那双不合脚的金绣花靴做了个交代。
匆忙之间拿错了花嫁鞋,这个解释倒是说得通,虽然有一些牵强,但一时也无可反驳。
所以,这绣鞋一事,也就暂且先搁着。
“好吧,无事。你等还为公主把鞋穿上吧,莫教她光着脚,走不过奈何桥。”
将绣鞋轻轻放在眉儿的手心里。
眉儿战兢兢走过了,哆哆嗦嗦地为仙仙公主穿鞋,却是无论如何也穿不上去,越是着急双手越抖得厉害。
马跃上前去帮忙着她,扶住了公主的脚,但眉儿依然无法为公主穿好绣鞋。
马跃一着急,索性将公主的脚提起使劲掰得弯些,一个掰一个扯,这才勉勉强强地将鞋穿好。
只是,可惜了一双价值连城的宫制绣鞋,被糟蹋得不成样子。
尉问天都不忍卒视。
“可惜了,公主国色天香……”大约是想起那粉色面纱下的脸着实当不得这“国色天香”四个字,于是住了口,耸了耸肩,又摆弄起他的兰花指来。
眉儿退至一旁,掩面而泣:“公主乃圣上掌上明珠,宫中人人怜爱,一心只想着风风光光嫁为大辽太子妃,今日落得这般地步,怎不叫人肝肠寸断?”
马跃在她身旁,又是一番好言相劝。
贺锦心将这一切看在眼里,默不作声。
夕阳斜晖打在万帐顶篷上,远处风沙渐起,沙尘被风刮过,渐欲迷人眼。
贺锦心仍然没有任何突破,只是慢慢地踱开了,在营帐之间徘徊。
马夫默默地跟着她的身旁,不远不近。
而她的身后,是一众人等一眨不眨盯着的眼睛,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坚持不懈地追随着她的身影。
龙珠太子的脸上已然浮起一丝焦虑。
尉问天满满的沮丧写在脸上。
耶律楚齐与耶律楚成则显得悠闲得多,抱着双臂,一副看热闹的神情。
日已将落。
现在,营帐前停放了三具尸体。
两位公主一边,木昆放在稍离远一些。
云朵公主眉心紧蹙面貌呈痛苦之状,仙仙公主虽然蒙着面纱,然而双目微睁似有吃惊之意。
这两位美人公主生前不管如何明争暗斗,到得今时也不得不被搬至一处仰面朝天并排同卧。
只是两个侍女却是麻烦,三言两语不合便乌眼鸡似的打起架来。
相比之下那格玛要厉害一些,眉儿则显文弱了许多,被格玛推搡两下,便趔趄着连退了几步,鞋都掉了。
马跃急不可耐,但女子打架他又不好插手,只得一手护住了眉儿一边不住地叫唤:“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又见眉儿鞋掉了,急忙替她拾起,蹲在地上为她穿上。
眉儿金鸡独立且是不稳,晃了两下,马跃又是贴心地扶住她手臂,稳了下来。
只不过锦心注意到了马跃扶住眉儿的时候,眉儿急促地呻吟了一声,马跃立即现出一副歉疚之色,象是抓疼了眉儿手臂。
“贱婢,装什么狐媚相……”
格玛两手叉腰,指着眉儿怒骂,却忽地住了口,“咦”了一声,目光落在仙仙公主身上半晌没有闭上嘴。
“有什么不对吗?”
锦心看格玛神情有异,索性将她拉了过来,凑近了仙仙公主,好教她再仔细看个明白。
“不对,这不对。”格玛细细看了一番,指着仙仙公主嚷嚷起来。
“啥不对?难不成这不是仙仙公主?”
尉问天嗤笑起来,免不了也凑近了看了又看。
“还是她呀。这不到一日功夫,能诈尸还是变妖怪?”
格玛手依然指着仙仙公主,却迟迟说不出哪里不对,只是不停呢喃着,总之就是有哪里不对。
“反正我家云朵公主就是没有杀人……”
尉问天被她一乍一闹的,实在是心烦,厉声训斥:“杀没杀人不正在查吗?闹什么闹?有完没完?再闹就将你带下去。”
格玛无奈,只得又是抽抽嗒嗒地站一边去,然而双目如利剑般斜刮着眉儿,令眉儿浑身十分不自在,不由得往马跃身旁靠了靠。
“闹够了吗?闹够了都给本王保持安静,否则通通带下去。”
龙珠太子终于按捺不住了,这个“通通”包括了刚才大声嚷嚷的尉问天,也不理会他又是翻白眼又是跺脚的。
“锦心小姐,辛苦你了。”
是客气,也是催促,但也只能安静等待。
锦心点了点头:“锦心尽力而为。”
夕阳已慢慢地移过了半个营帐,贺锦心围绕着两位公主走了一圈又一圈,忽而沉思,忽而凝眸,最后停在仙仙公主头前,目光移向尉问天。
这一回不等她开口,尉问天已经自动走了过来,歪了歪脑袋问道:“心心但请吩咐,小尉在所不辞。”
锦心指了指仙仙公主脖颈处,尉问天旋即明白,兰花指又是一阵子比划,选好了姿势,才将仙仙公主的头拨开抬起了脖颈。
脖颈处的血迹已经完全凝固。
“能分辨出是刀伤还是剑伤吗?”
尉问天一仰脖子,毫不犹豫地回答:“刀伤。”
将纤纤手指在仙仙公主伤处比划了一下,又后退一步眯缝着眼瞄了几瞄,还煞有介事地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而后双手背在身后,踱起方步,神气十足地分析道:“此伤口粗重宽厚,而刀口平直,并非大辽士兵惯用的‘肩二枪’与‘斧刀’,而更倾向于汉人所用直刃直身直柄刀……”
此言一出,格玛旋即大放悲声,朝着龙珠太子跪下哭诉:“我家公主用的是三寸尖,大家都有目共睹,小小的薄刃怎弄得出那宽厚的刀伤来?那仙仙公主实非云朵公主所杀,求太子殿下明鉴,还我家公主清白。”
龙珠太子点了点头,他的目光很快就锁定在了马跃的身上。
这里带直身直柄刀的汉人,只有马跃。
昨夜他在“月下漫步”之时,见识过马跃的所谓“龙错震”以及那把镶嵌着绿色宝石的赝品“鸣鸿刀”,刀身确实有几分厚重,也需有足够的臂力才能够使得起。
昨晚围观马跃月下耍宝的辽兵,足有十余多人。
“这位兄台,可否借你的宝刀一观?”
尉问天虽然出言彬彬有礼,但却是不容否定的。
马跃的神情立即显得几分慌张起来,一连退了几步,一只手握住了腰间刀柄,没有依言将宝刀借给尉问天“一观”。
然而马跃越是慌张,就越引起众人的怀疑,他一步退,众人就一步进,辽兵已然呈四面包抄之势。
小蚯蚓警觉地挡在了龙珠太子跟前,同一瞬间,尉问天的纤纤手指一挥,所有兵丁一拥而上。
马跃双脚一弹飞身向上,正要借着一个营帐顶篷垫脚逃去,却只见一个小石子儿飞出砸在他的膝头上。
马跃应声滚落下来,随即翻身爬起,但未及拔腿出逃,已被训练有素的兵丁们狠命地摁倒在地,动弹不得。
眉儿哇地哭声震天响。
唯有一个人看清了那只小石子的出处,但他只是皱皱眉头,没有吭声,只是面色显得更加地凝重与忧虑。
“不是我,不是我,我怎么可能杀害仙仙公主?冤枉啊,本人不服,不服!”
马跃被摁趴在地,努力地抬起头来,声嘶力竭地喊冤。
“不是你逃什么逃?显然就是做贼心虚。被捉住了就喊冤,你当众人都是冤大头啊?”尉问天走上前去,用他那尖尖的兰花指狠狠给了马跃一戳。
耶律楚齐与耶律楚成两位皇子这热闹是看得津津有味。
然而这一场热闹之中,唯有一个人仿佛是置身事外,那就是沉默寡言的马夫,看起来他对任何事都显得无动于衷,大有一种“热闹是他们的,我自清悠”之高境。
当然,除了那颗他忍不住从地上拾起又飞向马跃的小石子之外。
尉问天斜睨了龙珠太子一眼,难掩一脸的兴奋。
先是吩咐兵丁将马跃捆好了,同时也不忘吩咐众人看管好眉儿,安排妥当了之后,这才慢悠悠地看着马跃,说道:“服与不服,待本军师将原委说个一清二白,到时众人听过之后就明白你是冤与不冤,也好叫你心服口服。”
尉问天将假“鸣鸿刀”拿在手里把玩,但那刀很沉,他不得不用两只手紧紧握着才握得住,于是就索性抵在地上,当做拐棍来支撑,而后清了清嗓子,这才开始慢条斯理地阐述他的道理。
“一切的缘由,皆因这位眉儿姑娘而起,马跃,我说的没有错吧?”
眉儿原本低头哭泣,猛然间被提起名字,吃了一惊抬起头来,只见她面色煞白,双唇颤抖,拚命地咬住了嘴唇。
马跃低下了头,但依然倔强地回答:“休要瞎扯,此事与眉儿无关。”
尉问天一边玩着假“鸣鸿刀”,没有理会马跃的辩驳,继续神采飞扬地向着众人阐述。
“人生自是有情痴,一个是宫廷侍卫,一个是妙龄宫女,在清规森严的宫廷之中,天长日久暗生情愫,在本军师看来,这些都情有可原。然而仙仙公主却是理法有度,怎么容许如此有违宫制之事发生在眼皮底下?棒打鸳鸯在所难免,更兼因眉儿拿错了公主的嫁鞋,受到公主的责罚,因此侍卫暗生恨意杀心顿起,竟然对公主狠下杀手大开杀戒。”
“于是……”
尉问天忽地一顿,盯住了马跃的眼睛,令他避无可避,将那慢悠悠的腔调发挥得抑扬顿挫起来。
“昨夜仙仙公主与云朵公主起争执,眉儿无端遭受池鱼之灾,令你终于下定了决心,将仙仙公主杀害以为眉儿报一箭之仇。”
龙珠太子及两位皇子的目光紧紧跟随着尉问天,令他受到了鼓舞一般,越说越觉得兴奋起来,眯缝着双眸凑近了马跃,时而又拿眼斜觑了眉儿两眼。
“马跃身为北汉皇家带刀侍卫,功夫自不必说,据我所知,还自创了什么‘龙错震’,在大辽士兵面前很是露了一把脸面。试想想,如此自命不凡的人物,为何不在大白天人多时耍宝,却要在大半夜邀木昆来什么‘月下切磋’,岂不是有悖常理?这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好叫众人以为他忙于耍宝,没有功夫杀人。”
“之所以嫁祸于云朵公主,一者,为自己开脱,二者,北汉既与大辽联姻不成,突厥也休想渔翁得利。另则,公主仙逝,太子大婚未成,则侍卫与宫女没有留下的必要,大可远走高飞双宿双栖。只是……”
尉问天一口气说了这许多话,停下歇了歇,吞了一口唾沫,双目炯炯又重新盯住了马跃。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枉你们算破了天,遇到了我神算尉问天,如意算盘也叫你们鸡飞蛋打。杀人害命,罪责难逃,弑主嫁祸,更是罪不容诛。至于云朵公主之死,则完全是因为她自身的心疾,也就是痛心病,大家看她的死状,做捧心之势,这就是心痛至极的痛苦之状。”
尉问天侃侃而谈,时而抑扬顿挫,时而手舞足蹈,众人安静聆听未有疑义,格玛也频频地点头称是。
直至说到云朵公主的死因,又模仿云朵公主的死状做了个捧心之势,格玛却不乐意了,嚷嚷了起来。
“不,不对,云朵公主从小到大从没有过什么痛心病,身体硬实的很呢,从日出骑马至日落捕猎射箭,都不曾喊过一声累的。”
“暗疾,你知道什么叫做暗疾吗?”尉问天厉声喝住了格玛。
“正是日日骑马投射捕猎,非一般女子身体所能承受,长此以往造成的暗疾。也因云朵公主性格刚毅,一点小病小痛就扛过去了,以至于没有人发现她实际染有痛心之疾。只可惜昨夜她心疾发作之时身边无人知晓,否则当即施以援救,应该还不至于死翘翘。”
尉问天的解释似乎不无道理,两位皇子均点头表示赞许,无奈仍说服不了格玛。
只是格玛左想右想的,却也想不出有什么不通之处,没了言语来反驳尉问天的定论,一抬起看到眉儿一张梨花带雨的粉脸,胸中怒火顿时熊熊燃起。
“我不管你怎么说,公主哪里有什么暗疾?一定是这贱人与她奸夫共同谋害了的,好让他们家公主当上太子正妃。”
一头哭着一头向着眉儿猛扑过去。
眉儿冷不防之间,被格玛揪住了头发,扭着身子撕扯起来。
一时之间两个女人的哭叫怒骂之声不绝于耳。
“放开她,你这贱婢,休得欺她。”
马跃见眉儿吃了亏,也顿时神经炸毛起来,但因双臂被反捆了又在兵丁看押之下,动弹不得,只能张着一张大嘴怒目而向。
“嗯呵……”
尉问天咳嗽了一声,给左右兵丁使了个眼色,兵丁使了蛮力,才将两个扭打在一起的女子分开。
格玛不肯善罢甘休,叉着腰,依旧怒骂不止:“不把这一对狗男女千刀万剐,格玛我不服、不服。”
龙珠太子终于按捺不住,恼怒地挥了挥手,尉问天厉声喝道:“带走带走。”
兵丁立即遵命强扭了格玛就要带走,格玛犹自挣扎不已。
二皇子耶律楚齐一直抱着旁观者的态度饶有兴致地看着热闹,此时却出人意料地开了腔:“云朵公主身故,侍卫又突遭杀害,格玛伤心急躁在所难免,也足可见其主仆情深,大哥就免与她计较了吧。”
又沉了声对格玛说道:“小蹄子,如今案情已是真相大白,还怕凶手不伏罪伏法不成?还不快快向太子殿下请罪?该有的公道,太子殿下自然都会一一地还给你。”
格玛本是性情桀骜不拘之人,此时却一反常态乖乖地听了二皇子的吩咐,朝着龙珠太子跪下身来磕头请罪。
龙珠太子原本宽仁,念于格玛刚刚失去朝夕相伴的主人,并没有真与她计较,此时见楚齐为格玛说情,也就顺手推舟,卖了楚齐一个人情,点了一下头:“保持安静即可。”
格玛恭敬起身,退到了一旁,再也不敢造次。
营账前变得安静下来,只剩下眉儿低低的抽泣声。
马跃虽被反缚着双臂,努力地将身体斜倾向眉儿的方向,对她说:“别哭,你别哭啊,忍一忍,就过去了。”
眉儿悲悲切切叫了声:“马跃”,泪如雨下,哽咽不能语。
“不,你什么也别说,咱行得正坐得直,若龙珠太子只听这鸟军师放屁,连公道二字都不识,也枉费了他‘仁明太子’的名号。”
马跃死到了临头,豁出了一条性命,什么都不顾了,只这一句话里,既讽贬了军师,又冒犯了龙珠太子。
尉问天闻言大怒,飞扬兴奋的神情逐渐地被义愤填膺之气所替代。
一旁看押的兵丁也恼马跃说太子坏话,将他胳膊使劲地反扭得更深些,只听得骨节“咔咔”地错位的响声。
眉儿哭得越发的大声:“马跃,你别说了,别说了。求你们放他松一些,求你们啦。”
兵丁们毫不客气,却将绳索捆得更加地紧实。
眉儿哭求无门,无奈之下,又只剩下放声大哭,若是平日里,这般娇弱的模样定叫在场人等恻隐之心大动,只是今时今日已非昨日可比了。
“好一对深情厚义的小男女,至情至性感人肺腑,本军师都快要被你们引得潸然泪下了。然而,毕竟恶奴弑主罪大恶极,罪不容诛,非情理可原。”
尉问天将那把假鸣鸿刀使劲地往地上一杵,陷入沙土之中足足三寸有余,也足见他手上的劲道非凡。
但他很快换了神情,在愤慨之后,渐渐地又被心中一缕轻柔的东西所替代,望着马跃与眉儿,轻轻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马跃,眉儿,虽然你言语中对本军师大不敬,但本军师并不与你计较。现本军师念你二人情深意重,就僭越了太子殿下擅自作主给你们一夜做最后的话别吧。”
龙珠太子稍稍一震,眉心有些微的轻皱,面带不悦。
而尉问天根本连瞅都不瞅他一眼。
实际上,龙珠太子的不悦,并非尉问天的所谓僭越,而是这位向来与他没有主宾位分之别的军师,从来没有因为僭越而客气过。
而现在,却是一口一个“太子殿下”地叫着,言语之间处处显得生分。
只因先前说了他一句瞪了他一眼而已,竟然怀恨至此,也足见他有多么小心眼。
“我俩于宫中日夜相守,日久生情,这些我都承认,也曾想双宿双飞,但绝然没有想过去杀人,就算现在刀架我脖子上,我也只有一句话——没有杀人。”
“马跃,铁证如山,已不由得你强词狡辨,带下去吧,眉儿也带走,休得在此抽抽嗒嗒地,烦人。”
尉问天向着两位皇子抱了抱拳,说道:“真相已大白,因战事吃紧,就不多讲究了,明日就行刑,烦请王爷带上这厮的脑袋,还有这女子,回上京交了他们送亲使者带回北汉处置去吧。”
三皇子耶律楚成对于尉问天这种没有高低位分的行径非常不满,平日里与龙珠太子随随便便也就罢了,现在竟然使唤起二位王爷来了。
“这与我无关,我是来喝喜酒的,没酒喝也就罢了,难不成还带着颗脑袋回去?要带二哥带去。”
二皇子耶律楚齐怎肯吃他这一套,当即表示拒绝。
兄弟二人及尉问天又为了谁带马跃的脑袋回去交差而争论个不休。
龙珠太子闭眼深呼吸,摇了摇头,悄然远离了他们。
直至这时,他才发现,贺锦心已经很久没有说话了。
她依然站在两位公主的遗体旁,长久地凝视着,陷入深深的沉思当中。
那位满脸黑灰的马夫,此刻正呈半蹲之势,俯身面向仙仙公主,亦是长久地凝望着仙仙公主的伤口。
龙珠太子暗暗地吸了一口气。
这种半蹲的姿势,看上去十分平常,但普通人是决然坚持不了多久的,而这个马夫,却足足保持了有一盏茶的功夫,纹丝未动。
还有刚刚那颗凭空而起的小石子,虽不露声色,但还是没有逃过他的眼睛。
这大辽军营里,怎么忽然就成了卧虎藏龙之地?
近来因为被大婚之事搅扰得心绪不宁,对军营的管束有所放松,看来,是该要好好的整肃一番了。
马夫并不知道龙珠太子远远地盯着他的后背已经很久了,因为他的注意力完全放在那些凝结了的血迹上。
血柱的流势似有所不同。
“兄台似已看出,血流方向有所不同?”
贺锦心望着马夫,轻声细语。
马夫点了点头:“并非刀伤,而是剑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