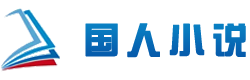2
他梳了韩式三七分,衬得一张少女欧巴的帅脸更加俊逸非凡,黑裤白T,领口松了两粒纽扣,露出精壮的胸肌,光是站在那里就是全场的焦点。
我捂住脸,此时此刻,只想找条地缝钻进去。
“别躲了,我是前男友,又不是催债的。”他开的玩笑还是那么冷,我家境不好,父亲外赌,没少欠钱,家门经常三更半夜响个不停。
那一度是我的噩梦。
我依旧不回,索性装死,他直接上手一根根掰开手指,仿佛我们的关系不曾变过。
不,他变了。
他的指尖多了几道粗粝的厚茧,在我发间穿梭,技术也比之前更娴熟。
不对,我不是要剃光头吗?
他怎么给我刘海梳到两边,半扎半散,口袋里抽出一条白色丝带在身后发髻系了个蝴蝶结?
从头到尾不到二十秒,他剑眉冷凝,对着镜子打量,双手自然地压上我肩,“怎么样?”
我眼神躲闪,起身划开手机,张了张嘴,他说,“没按顾客需求,免费。”
3
出门前,他又送我一张电子VIP,提出加微信才能操作。
本想拒绝的,可见他板着脸,一副阴沉得能滴出水的模样,我还是妥协了。
把他放出了黑名单。
他的控制欲还是跟以前一样。
记得初见沈淮南,是闺蜜子秋的婚礼。
闹钟坏了,我匆匆收拾穿伴娘服出门,叫车去现场只用了十分钟不到。
婚礼还有一分钟就开始,我的头发乱成一堆狗窝根本来不及收拾,我含着泪,为自己跟闺蜜的友谊的小船即将打翻着急跺脚,沈淮南长臂一揽,大手拦住我窈窕的腰肢,瞬间斜角四十五度摆出一个极其暧昧的姿势。
“给我半分钟。”
当初他也是莫名掏出一把木梳、一条丝带,左右捯饬给我梳了这个发型,还说我长发的样子很美。
那天,很多人这么说。
包括子秋和她老公——沈沂南。
沈淮南的亲弟弟。
4
“世界真小,蓓蓓你要开桃花了!”子秋拉着我的手,满脸要做红娘的样子,“沈淮南跟我们一个高中,一个大学,大两届,学习期间论文发了十几篇,国奖年年有。刚毕业在江城最大造型设计公司实习,听说那里老总对他青睐得不得了,前途不可限量,你可要好好把握!”
“你、你胡说什么呢?我、我和他怎么可能?”我虽是这么说,但不可否认,沈淮南很优秀,加上轮廓分明的脸庞,浑身上下的桀骜不驯的气质,我说一点不心动是假的。
为了道谢,食品专业出身的我总会给他带些自己做的甜品,夹杂了一点私心。他一开始是不吃的,有几次直接丢进了垃圾桶说不想做我的试毒机器,我和他不过多见了几次面的陌生人。
直至子秋夫妇约我们去新开的游乐场。
到了八点,仍不见人影,打电话也不接,我和沈淮南等了一个多小时,等到海枯石烂,最后他双手插在裤袋,“走吧。”
“啊?”
“别管那个臭小子,来都来了,逛逛。”
我挽了挽发,颇有些尴尬。
闲逛一整天,我们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十句,但谁都没有说要走,临近夜里,子秋给我打电话,“蓓蓓,你和沈淮南呢?我俩都在这里等你们半个多小时了。”
我看了眼表,已是二十点四十。
我意识到他们约错时间,正要解释,沈淮南夺过我电话,“约的不错,不要有下次了。”
5
他嘴硬心软,最后答应陪玩。
听摩天轮售票员说爱人坐到最高处接吻就会永远在一起,子秋屁颠颠地拉着他老公跑了。
留下我和沈淮南两人大眼瞪小眼。
他望着前方,心思明显不在我身上,我失落却无可奈何,找了借口离开,他买好票追上来,将其中一张塞到我手里,没说一句话,朝摩天轮走去。
我顿了顿,开心跟上。
缓缓升起,窗外的景色变幻,恰如我此时的心情。
沈淮南坐在我对面,我假装看别处,眼角的余光却禁不住偷睨过去。他轮廓凌厉,浓墨似的瞳仁如深渊漩涡,侵略性十足,此时正双手环胸垂着眼,长而密的眼睫毛落下一片阴影。
狭小逼仄的空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安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我抿了抿唇,低头假装刷视频避免自己拙劣的心绪被他看出。
噗通噗通,我根本无法冷静,摩天轮升到空中,慢慢不动。
啪嗒一声,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弥漫开来,紧接着是剧烈的倾斜!
“啊!”我下意识尖叫,整个身子落入一道温暖的臂膀!
我怔愣一秒,惶恐又激动地抬起脑袋,看不清沈淮南的表情,只能感受带有他温度的呼吸。
我心跳加速,几乎要跳到嗓子眼,有那么瞬间,我竟自私地希望多停电一会儿。
一分钟后,眼前一亮,我缓了过来,跟沈淮南四目相对,他眉头轻皱,眼神没有明显波澜,玫瑰色的薄唇微启,“痛。”
“什、什么?”
“我说我的脚痛。”
我尴尬地弹跳起来,坐得离他远远的,脸上红晕,晕染到了耳后根。
5
从那以后,沈淮南没再拒绝我的投喂。
我们的关系好像进了一步,一起看书、学习、游玩,美食打卡,好到沈沂南都争风吃醋,“不要不要,我不要余蓓蓓做我嫂子!哥你不听劝我肯定在你们的婚礼上哭得最大声!”
沈淮南没否认,我喜出望外,想他是默认了我们的关系,只要捅破那层窗户纸就能收获爱情。
一次给他当小白鼠,他用木梳一遍遍梳理,趁他半蹲下来到跟前时,我终于鼓足勇气俯身,唇碰了碰他的脸。
我本以为沈淮南会有什么表情,或愤怒或不高兴,但他始终没有回应。
事后,我跟他道歉,他整理工具,漫不经心地说,“没事,习惯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他将那把常用的木梳送给我,紧皱的剑眉慢慢舒缓,嘴角弯出淡淡的弧度,“余蓓蓓,想试试吗?”
他摸了摸我的头,用食指轻轻戳了下我鼻尖,暗示得不能再明显。
“嗯!”我抱住他,欣喜若狂。
都说爱一个人会不自觉变成对方的模样,那段时间我们如胶似漆,但热恋总有结束的时候。
我原以为我于他而言是窗前陪伴的灯火,可后来发现只是瞬间绽放的烟花。
不,或许连烟花都算不上。
他没有公开我们的关系,除了他弟弟,他的家人、朋友,一个都不知道他有对象,我好像是他见不得人的情妇。我发的消息他从不秒回,过生日问他今天什么时候下班,他结果过了两个多小时才回了没空,我去他楼下,发现他正跟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搂搂抱抱。
我不懂自己对沈淮南到底算什么。
我开始变得小心翼翼。
我不止一次暗示,“那个跟你聊天的头像好可爱啊,是工作同事吗?”
“今天我做了大餐,你晚上不回来吗?要去哪里?”
“我身体不舒服,你能帮我买点药吗?”
每次他的回答只有简短的‘嗯’、‘工作’、‘忙’,家里的失望攒够,我离开了。爱情的失望漫出来,我看开了,没像别的小情侣那样吵得要死要活,我跟沈淮南就此桥归桥、路归路。
后来他分手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向前看吧。”
我欣然接受,微笑道,“祝你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