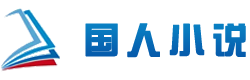太极宫。
大殿四周古木参天,宫门楼宇鳞次栉比,殿内雕龙画凤,金碧辉煌,也只有长安内的皇城有这样的气派。
皇帝李忱正翻阅着京兆府尹递呈的奏折,脸色沉郁,越看越气,最后终于忍不住重重扔在地上。
左神策都尉王宗实慌忙捡起折子,道:“大家又在想那件案子了?”
李忱竖起剑眉,怒道:“这青天白日的,京中竟有两个银柜被盗了!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就敢犯案,朕还拿他毫无办法,你说,这要朕以后有何颜面面对tai祖皇帝?”
王宗实宽慰道:“大家千万息怒,小心伤了龙体。”
李忱又怒又气:“你说这个韦澳,他平时忤逆朕,朕念他有些才能,便纵着他,不与他计较。可如今,朕把这么重要的案子交给他,他却数日给不出个结果,同那些酒囊饭袋有何区别!”
王宗实为李忱斟上一盏茶,思忖一番,道:“大家先消消气,此案却是要复杂些,可这韦府尹不行,不还有沈娘子为您分忧吗?”
李忱拿起茶盏,听到王宗实的话,手上一顿,复又将茶盏放回桌上,不悦地道:“哼,她也不叫朕省心。”
王宗实低头站在一侧,试探地问:“大家是在怪沈娘子得罪了郑国公那边?”
李忱喝了口茶,瞥他一眼,道:“你懂什么?”
王宗实赶忙把头一低,小心翼翼地道:“贱奴愚钝,自是读不懂大家的心思。”
李忱看他:“这沈丫头如今还在申州办案呢,你好好的,提她做什么?”
王宗实眼珠子一转,窃喜道:“奴才不敢瞒大家,沈娘子今儿一大早便在太极宫门口候着了,只等大家下了朝前来拜见。”
李忱正翻看着折子,听到此话眉头一皱,道:“你怎么不早说?”
王宗实低头道:“这是沈娘子吩咐的,说自己是有罪之人,此次前来一是想帮大家分忧,再则,便是来请罪的。”
李忱把手中的折子一放,就着王宗实端来的金盆洗了洗手,道:“叫她进来。”
王宗实道了声是,欠着腰端着盆子出去了。不多时,便见沈玉书着着一抹淡绿走了进来。人刚站定,便行了个大礼。
“玉书参见主上。”
李忱抬头望了她一眼,“回来了也不跟朕说一声?”
沈玉书双手作揖,垂着头道:“玉书……自知没脸见主上。”
李忱神色未变,道:“你做错什么了?”
沈玉书把头低得更低,“玉书明知那庄生是郑国公府上的门客,却还是不顾情面定了他的罪,得罪了郑国公,还驳了太后的颜面,让主上……”
李忱眉毛一挑,道:“那你说说,你何错之有?”
沈玉书一顿,小声的:“玉书错在不该让主上难做……”
李忱轻笑了一声,无奈地摇头:“起来吧。”又给玉书赐了座,吩咐御膳房的厨子备餐,将御膳挪到太极宫来,才又道:“你若也学了那些个无用的做派,这个祖宗的法度做给谁看?”
沈玉书被说得羞红了脸,微微躬身道了个万福,便坐下了。
之后,二人便再无言语。待御膳上来,三杯酒下肚,李忱这才又说了一句:“这两月吃了不少苦头吧?”
沈玉书莞尔:“这是主上对玉书的历练,玉书心中甚是感激。”
李忱笑:“出去一趟,学了什么本事不知道,倒是学来了一堆没用的奉承话。”说着,从八彩琉璃瓮中舀了三勺燕窝羹递给沈玉书,道:“吃了。”
沈玉书接过碗,认真的:“玉书自小便在主上身边长大,主上对玉书的好,玉书无需用那虚假的体面话来奉承,玉书是打心底里感激主上的。”说罢,舀起燕窝喝了一口,小孩子似的笑道:“主上,还是长安的燕窝好吃。”
李忱宠溺的一笑,道:“在朕身边,没必要那么拘谨,若还想吃什么,朕让御膳房的厨子们再多做一些来。”
沈玉书笑着连连点头,那碗里的燕窝掺了蜜似的,让她的笑里都带着甜。
皇帝看着玉书,竟一时有些恍神。不知何时,他养在身边的这个小丫头,竟然也出落成了如今亭亭玉立的模样。他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玉书时,玉书还尚未及笄,也不若如今高挑,却凭着一股聪明劲儿就让他喜爱万分。
大中元年初,有个波斯使臣来大唐朝贺,酒席间使臣喝的半醉,趁着酒兴,他突然说自己手里有一个难题,大唐绝对无人能解开。
李忱问是什么问题,使臣让人拿出一个西瓜,问里面的瓜籽有多少颗,但不准剖开去数,让大臣们尽管商量,最后只准说出一个答案来。
如此刁钻古怪的问题果然没有一个人回答的出来。恰好那时沈宗清带着沈玉书出来戏耍,她见众人眉头紧锁,突然站起来说:“我知道!”
所有人都看着她,使臣也瞪大了眼睛。
皇帝大喜,问她有什么办法。本以为她要细细算上一番,谁知她却一脸稚气的说根本不用看,只需用手摸一摸西瓜,西瓜自会告诉她。
众人大惊,只见她果然伸手摸了摸西瓜。
使臣吃惊道:“小娘子,那你说说看瓜籽有多少颗?”
沈玉书眨眨眼,想都没想,道:“我早就知道了,瓜籽整好有一百五十三颗。”
众人皆错愕不已,那西瓜完好无损,难道她有隔板猜物的本事不成?就算能看的到,那么多瓜籽少说也得数上半个时辰。
使臣笑了,道:“你这么肯定?一颗不多一颗不少?”
“当然。”沈玉书点点头,于是圣上便要人过来切瓜,她却笑了,说:“主上等等,切瓜之前我想和使臣打个赌!”
使臣惊讶,道:“赌什么?”
她笑着说:“我要是输了,阁下就得当着所有人的面夸赞我大唐比你波斯繁盛,我要是赢了,便当着所有人的面学狗叫,阁下看如何?”
沈宗清听完,脸上已然像是泼了泥彩。
此时,使臣的脸上更是难看,道:“你这赌注有问题。”
沈玉书天真地笑:“哪里有问题?”
使臣脸色不好地道:“你这是变着法的侮辱我波斯国的颜面,我怎能答应?”
沈玉书眨了眨眼睛,道:“回使臣,只要我没输,阁下不就不用承认我们大唐比你们波斯厉害了?还能看到我学狗叫,这赌注哪里有问题了?”
使臣的脸色越来越黑,却终究也没再说什么。
“现在可以切了。”沈玉书无比自信地看着使臣,使臣想了想,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道:“圣上,不用猜了,是这个小娘子赢了。”
“阁下认输了?”沈玉书道。
使臣脸色并不好看,他点点头。
沈玉书道:“我说了,我赢了我就学狗叫。”
她果然学着小狗叫了几声,又冲着使臣做了几个鬼脸,却很可爱,谁也没觉得奇怪。
李忱道:“你还没切呢?得数数才知道。”
大臣们也是面面相觑。沈宗清低声问道:“你怎么就知道瓜籽有这么多颗的?”
“阿耶,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不过巧的是他也不知道。”她指指使臣。
李忱得知后,惊讶问道:“你是瞎猜的?”
“是。一个没有切开的西瓜,不论是谁都是不可能知道瓜籽数目的,出题的人当然也不知道,可是人们总是觉得他肯定知道,所以没有一个人敢说,只要没人猜出答案,出丑的就是大唐了。”她又道:“于是我就随意说了个数字,当然,这并不足以让他退缩,我还找到了他的一个弱点。”
李忱笑道:“所以你就以波斯国的颜面做赌注?”
“是的,他是波斯国的使臣,为了保住波斯国的颜面,他定然不能让我输。而我只要不输,咱大唐便赢回了颜面!”沈玉书得意地说。
李忱看着这个小女孩,喜欢又欢喜。
那一年,小小的沈玉书得了个威风凛凛的封号,“天下第一才女”,乃当朝皇帝李忱亲封。
时至今日,李忱依旧记忆如新。
当然,沈玉书也确实没有辜负这“天下第一才女”的称号,短短几年,已经办了不少奇案。此去申州,更是顶着郑国公和太后的压力,关押了其门客庄生,替甘露之变时被无故牵连的白家翻了案,还查问出了李郑余党的下落,令李忱甚是欣慰。
两人一直聊到申时,玉书几次想与李忱谈起长安最近发生的几起怪案,每每开口,却都被李忱制止了,只让她早些回去休息,明日午时再来含元殿找他。
沈玉书几番欲言而止,只好听命告退。
出了太极宫,没走几步远,王宗实便喊住了她。只见他的手里正拎着一个鸟笼子。
王宗实是李忱身边的宦官,早些时候在御膳房供职,因为做的一手好菜色,颇受李忱赏识。就这样,他平步青云,顶了御膳房总管的位子,不久又升为左神策都尉,手下握有五千神策军,在宫中颇有些权势,朝中大臣都尊称他一声王贵人。
“沈娘子且等等。”王宗实道。
沈玉书停下,目光落向他手里拿着的鸟笼子,有些疑惑地问道:“王贵人这是?”
王宗实捏着嗓子笑道:“这是圣上前几日去燕林狩猎时捕到的一只百灵鸟,圣上念沈娘子此去申州有功,便把这鸟赐给了您,说是您日后破案无聊时还能拿它解解闷儿。”
沈玉书微微颔首,道:“那就有劳王贵人。还请王贵人回去代我谢过圣上。”
“好说好说。您如今可是圣上身边的大红人儿,老奴可担待不起,只望以后沈娘子别忘了老奴的好才是。”他眯着眼睛,扯着细细地公鸭嗓子,把老太监溜奸耍滑的模样表现的淋漓尽致,道:“圣上还在殿里,我便先走了。”
“王贵人请便。”沈玉书笑了笑,便转身上了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