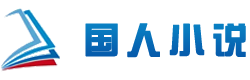前传第5章
韩二小姐(1)
回家到之后,曾隅躺在床上结结实实的睡了个昏天黑地。第二天才想起,得给奶奶交代一下自己已经回来,然而并没有找到曾戚。
往乡下老家打了通电话,才听说曾戚已经回家。
这厮向来想一出是一出,走之前给自己留了个条子,说要去雪山历险,结果到了喀什,又听说叶城有个什么庆典,就改了主意跑去叶城看热闹,连雪山山脚都没走到。
曾隅气得咬牙。
自己九死一生,结果就为了这么个二不挂五的东西,想想都不值。
不过听到曾戚平安,曾隅也觉得松了口气。
可有一件事,却让他有些为难——
奶奶让他回趟老家。
曾隅父母早逝,小时候跟着奶奶一起生活,奶奶是旧社会大家庭出身,对他十分严格。虽然从不打骂,但也从不亲近,大多数时候曾隅有些怕她。
奶奶虽然是自己的奶奶,但更是韩二小姐韩佩瑜。爷爷是韩家倒插门的姑爷,去世得早。曾隅对他的印象很模糊,只隐约记得他身形清瘦,举止温柔,喜欢吃金钩煮粥。
父母去世以后,奶奶就把曾隅接到韩家,之前对母亲的诸多不满意,便体现在了他身上。
曾隅那会儿才几岁,寄人篱下,万事都得小心翼翼,容不得错,就算是被韩家旁系的小辈欺负了,也不好吭声。
老实说,那并不是一段非常好的回忆,以至于曾隅到现在都有些抗拒韩家老宅。
可是韩二小姐从来说一不二。
没办法,曾隅只好动身回家。
韩家老宅在鸣岩山中,山下村子里的人也姓韩,算是韩家的旁系。上山没有可以通车的路,只能步行。曾隅到的时候,天都黑了。
还没等进到堂屋,就听见曾戚讨饶的声音:
“妈你别打了,再打我就死了!”
韩佩瑜笔挺的坐在中堂方桌右边的圈椅上,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拿着根细竹条,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曾戚规规矩矩的跪在她面前,一脸要哭不哭的样子。
说到这个小叔,是出了名的不学无术游手好闲,仗着爷爷留给他的几处房产,愣是糊涂着过了半辈子,成日只知道寻欢作乐游山玩水,年轻的时候闯出不少祸来,现在都快四十了,依旧死性不改。
不过曾戚混账归混账,面对老娘还是任打任骂的。竹条打在他身上,也不躲,疼的龇牙咧嘴嗷嗷直叫:
“我错了!我错了!妈,打在儿身,痛在娘心,诶哟!疼!”
不论曾戚如何讨饶,韩佩瑜依旧是一副冷冷清清的表情,手上的动作也不停,一下一下打在曾戚身上。
老宅不通电,堂屋里只点了几根蜡烛,烛光照在韩佩瑜有些许皱纹的脸上,依稀能看出年轻时候的美貌。岁月对她已然十分宽厚,毕竟过了年,韩二小姐就七十岁了。
“知道错了?”韩佩瑜问。
“知道了知道了!”曾戚认错认得爽快,但从来都是死不悔改。
曾隅深知他的性子,抬脚进了堂屋,对着余怒未消的韩佩瑜喊了声:“奶奶。”
韩佩瑜看了曾隅一眼:“回来了。”
语气冷淡疏远,丝毫没有奶奶见到孙子的喜悦。
反倒是曾戚,见了曾隅像是见到了救命稻草,立刻喜形于色的从地上起来:“大侄子,你怎么来了!”
“让你起来了吗?跪好。”韩佩瑜一双美目扫过曾戚,呵斥道。声音不大,却颇有威严。
曾戚刚有点嚣张起来的气焰,立刻就被浇灭了烟都不剩,不情不愿的回到原地跪好。
“你表哥也回来了,一会儿去见见他。”
“是。”曾隅说。
他和奶奶一向没有什么交流,即使是有,也是客气而冷淡的。
韩佩瑜挥挥手,示意曾隅可以退下了。曾隅点头,临走时看了跪着的曾戚一眼,对方正挤眉弄眼的看他。
奶奶口中的表哥是韩家老大的孙子韩准。曾隅和他算不上亲近,以前住这里的时候也并无太多来往。只记他身体不好,不太爱说话,整天捧着书看,和一帮皮孩子比显得尤为沉稳。
上了初中之后曾隅就一直住校,见这位表哥的机会更是少了。后来听说韩准考上了一所十分不错的大学,毕业之后留在了省会锦城。
到了韩准房间,曾隅敲了敲门,房门很快就开了,里面的人掌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从灯光里露出一张苍白的脸。
见是曾隅,韩准笑了笑:“你来了,快进来,外面凉。”
说着就拉起曾隅的手引他进了房间。
韩准十分清瘦,气质有些阴柔,穿着一身深蓝色中式的棉布衣服,衬得脸色更白。在灯下看有种不似人间的飘渺感。那只握着曾隅的手骨骼分明,触感却十分冰冷。
“那个......奶奶让我来见你。”曾隅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没喊出那声“表哥”。
“很多年没见,你长大了。”韩准这话说得老气横秋,实际上他也只比曾隅大了三岁而已。
曾隅一言不发,他不记得和韩准之间有什么值得叙旧的事,听到这样的开场白,免不了尴尬。
没得到回应,韩准也没有表现出不高兴。他那双眼睛生得极好,瞳仁深黑,盈盈泛着水光,怎么看都含情脉脉。
曾隅被这双眼睛盯着,只觉得脸上发烫。赶紧说:“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韩准僵了一下,继而又恢复了落落大方:“确实有件事,想要拜托你。”
“什么事?”
“咳咳、咳。”韩准突然剧烈的咳了起来,苍白的脸上泛出不正常的红色。
曾隅赶紧把案头上的香炉点燃,灰白的烟从香炉的孔洞中袅袅升起,室内顿时就充满了似有若无的奇异香味。韩准止了咳嗽,轻喘着气看着曾隅,虚弱的笑着,眼睛却更亮了,像是有些惊喜:“你还记得这个?”
“小时候看鲁叔叔点过一次,说是治你病的药。”曾隅说。
韩准这病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治不好只能吊着,成日咳嗽不算,右耳还聋,一直带着个黑色助听器帮助听力。
曾隅见他还是有些喘,便站起来,轻拍着他的背帮他顺气:“这么多年,怎么不见好。”
“好不了的。”韩准不以为意,“病了二十多年,早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