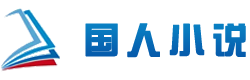这个世界最让人尴尬的两件事,一是当你穿得乱七八糟最不想见人的时候居然碰到了熟人;而比这还可怕的就是你无意中撞破了熟人的奸情。
2013年的冬天,李晓枫就同时撞到这两件尴尬的事。
她穿着睡衣遇上了最不想遇到的一位熟人,而且这位熟人还暴露了他最不应该在李晓枫面前暴露的小秘密。
本来是碰不上的。原来公关公司帮李晓枫订的是十一点的飞机,但谁知道北京12月的三十一天里倒有十来天的雾霾,晚上在活动现场试一款新出的鱼子酱面膜时,李晓枫感觉连气都呼不出来了——鼻炎犯了,打喷嚏打到全场侧目,最后只得躲到洗手间了事。
就在洗手间拼命用凉水冲鼻子的当儿,李晓枫叫公关公司的小姑娘火速把票改成了第二天早上八点,借口是想早点回去写稿。其实回去写个鬼,资料一早发回去了,新来的实习生钟露露是个勤奋聪明的孩子,估计明天晚上上版的时候改改标题就行。李晓枫就是想早一点走,离开这个鬼地方。
“北京果然是一个不旺我的地方啊。”李晓枫瞬间想起了刘裕德的那张方脸。尽管分手已经那么多年了,但李晓枫还是记得他永远紧皱的浓眉和薄情寡义的嘴角。是的,刘裕德就代表了北京这个城市最恶劣的那一面——现实、势利,要把每一个靠近的人榨得一干二净。这让李晓枫的心情更加恶劣起来。
“李老师,早上八点多的飞机,意味着您最晚早上五点四十就得出发,真的太早了。”公关公司订票的小姑娘善意地提醒李晓枫。
李晓枫微笑:“不怕,我平时就起得很早。”
是啊,早起可难不倒勤奋的《粤城新报》时尚部首席记者李晓枫。业内谣传李晓枫天天五点起来写稿——这也真是以讹传讹,只不过有几次因为下午要发稿所以早上五点起来赶过几次稿,就把同屋的同行们吓坏了。
2005年以后进入时尚行业的女孩们大部分是娇生惯养的中产女孩甚至是富二代,他们五零后六零后的父母撞正了时代,多少都发了点财,把所有的爱献给了自己的独生儿女。看着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长大,一心要见识一下五光十色时尚世界的掌上明珠们,哪里像李晓枫他们这些九十年代就加入这一行的老记者这么挨得和拼命。前者是为了理想,后者完全是为了谋生——报纸节奏快,当天的事情当天见报,当然要手快;而时尚杂志一个月才出一本,三月份的消息他们要五月刊才登出来,慢得要死。所以那些时尚杂志的小女孩一看到报社记者五点起来赶稿就觉得快疯了,真是少见多怪。
当然李晓枫也不介意这种以讹传讹,在这个圈子里,想要被人记得就要有一个标签。比如《京华快报》跑时尚的美女记者刘挺挺就以一撮彩色的“毛”出名,原本一个很文气的主播头,但她很“匪”地把左侧头发全部铲掉露出青森森的头皮,右额前方的一绺长发,今天染闪电蓝,明天染粉红,再配上她的黑色细条缠身皮背心,以及长靴和短裤之间那一段赛雪欺霜的雪白大腿,自带一种挥之不去的独特气质,让人惊艳。
有她的大长腿在先,别人就势必不能再走这个路线,好在女人除了腿还有胸,《新鲜时尚周刊》的女记者安吉拉以低V绝杀全场,每次出场必露乳沟三寸以上,双眼涂得黑雾迷离,把每个牌子的外国总监都看得目眩神迷。
而电视台大BOBO走的是丰满大模风,她一个人有安吉拉两个这么大,别人这么肥肯定难看死了,但大BOBO生得五官鲜明,当得起“盛唐美人”这四个字,而且她永远穿着来自云南的大袍子,黑的白的紫的蓝的红的,脚下再踏一双巴黎世家当季新款的黑白厚底鞋,一出场必然像一尾七彩大锦鲤跃入鱼池,把静悄悄的会场搞得水花四溅,认得的不认得的都给个热气腾腾的拥抱,怎么样你也难忘那销魂的挤压感……
你看,要在一个圈子里混出名,总归是要有绝活的。
李晓枫胸无四两肉,貌不出众,标签就是勤奋吧。虽然这个标签有点boring(沉闷),但胜在得来全然不费工夫,别人好意相赠,只好顺势笑纳了。勤奋就勤奋吧,总比说你土老肥好。这个圈子最怕的不就是土老肥吗?但偏偏又真戳中李晓枫的痛处。
有时候,李晓枫用她“尊贵的同行”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着实是捏了把冷汗:“土老肥”这三个字还真是跑不掉。
首先李晓枫肯定是肥的。小学的时候她得了一场肾炎,吃激素吃得肥成了球,然后这个肥就一直保持到了大学,导致李晓枫度过了四年黯淡无光的大学时光。
老呢也是真的是老。她入行的时候甚至连时尚这个行业都没成形,《ELLE》刚刚从季刊变成双月刊,林青霞老公的那个服装牌子刚刚进上海开店,路易·威登的广告词还是“旅游的真谛”,杂志上的女模特都化着浓妆,梳着大波浪、涂着鼻影、穿大垫肩的西装,最红的明星是江珊、王志文(很多人现在都不知道这两个人了),商场里播的背景音乐是《梦里水乡》,而报社甚至根本没有“时尚”这个版块。
土呢,就更没办法了。刚入行的时候有长达三年的时间李晓枫把“GUCCI”拼成“GOCCI”,刚开始她全部的时尚经验来自周蜜带她们看的那几部六十年代的奥黛丽·赫本的时装电影和图书馆里看到的《ELLE》《上海服饰》——这是当时国内仅有的两本可以称得上时尚的杂志——真是不敢和人说啊,但让一个出生在湖南三线城市炼钢厂的子弟懂什么叫时尚也真是有点为难,毕竟李晓枫一出生闻到的就是空气中无处不在的烟尘味,夹杂着煤味灰味土味钢铁味,那是钢厂生活的一部分。
说起来,连入这一行都是一个意外。
毕业三个月后,李晓枫失魂落魄买了一张火车票离开北京,南下广州时只带了一只背囊,袋子里有两件换洗衣服、一双高跟鞋,还有八百八十四块钱。是的,李晓枫是一个拿了八百八十四块钱在广州“白手起家”的女人。
记得那是整整一天两夜的绿皮火车,眼泪一刻也没有停过。到广州的时候,刚好是黎明,薄雾里缓缓映入眼帘的是窗边大朵大朵火红的吊钟花。啊,南方到了,这就是南方。李晓枫轻轻对自己说,这就是南方,南方会对我好的,《易经》上说了,南方属火,利女人。
她完美地错过了招聘季,万般无奈只得在周蜜的宿舍里借宿了半年。
周蜜有一个好爸爸,也有一个好男友,一毕业就分配到了广州商业局下属的一家外贸公司,那时外贸公司是最有油水也最有前途的单位。周蜜那间小小的单人宿舍堆满了花花绿绿的香港物资。“蓝罐曲奇,送礼体面过人。”这是周蜜教李晓枫的第一句广东话,也是李晓枫第一次吃到来自香港的食品。过了多少年,李晓枫也忘不了那浓郁的牛油香气。
那时内地的同学一个月才挣二三百块呢,周蜜的工资已然过千,还有各种各样补助和物资,外加工资一半的港币奖金。这套市中心的小宿舍,人家还不稀罕住。“大胡连洗脚水都给我倒好,”她跟李晓枫嘚瑟,“你呀,想住多久住多久!大胡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房子,谁让他在地产公司呢!”
李晓枫住了五天后,她又开玩笑似的敲打李晓枫:“晓枫,懂事一点,买点东西打点一下我们单位那些行政吧,不然他们要说我私自借房给朋友了。”李晓枫出去一打听,周围这样的单间小房子的租金是八十块,于是干脆给了周蜜一百块,说:“我不认识你们单位的人,以后我每个月给你这么多,要打点你就帮我打点吧,辛苦你了。”
周蜜推辞了一番,也就平静地笑纳了。
周蜜这个人就是这样,从来没有缺过钱,所以她从不明白钱对于一般人的重要。这导致她也体会不了对一个窘迫的女同学最好的关照不是请她吃蓝罐曲奇,带她一起逛街,送她一件衣服,而是实实在在少收她二十块钱,因为这个够她吃一个星期的饭。但周蜜对此一无所知——确切地说,她对和她无关的世界没有任何了解的兴趣,她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和她一样,随意吃蓝罐曲奇,逛街买一堆衣服,有一个宠她的爸爸和男朋友。如果没有这些,那就是不够努力和优秀,或者是没运气——不努力和优秀当然只能怪你自己,没运气更不值得同情,仍然只能怪自己。所以她收下一百块是正义的。一个人欠债要还钱,住屋要交费,这叫“公平”。但这种凡事力求的“公平”让她和谁都亲近不起来。不过她也不觉得自己和谁疏远。
“整个儿就是缺心眼儿,谁跟她交朋友谁傻。”李小贞背后说她。
但李晓枫还是把周蜜当成朋友。缺心眼的人也有缺心眼的好处,她不想那么多,就不容易受伤害,交往起来比较简单省力。李小贞看到天上的云淡一点都要写首诗:淡淡稀薄的云,像你的心……而周蜜看到稀薄的云眉毛都不动一下,她没有什么多余的感情,或者说她不允许自己有什么多余的感情,这样她的生活才日夜呈现出健康又明朗的态势:一是一,二是二,三下五除二,搞定!
有时觉得她心硬得可怕,可是一想到她是缺心眼的缘故,李晓枫就不跟她计较了,况且她收留过李晓枫这小半年,还把“肉多多”(一只金渐层的猫)送给她,李晓枫一辈子记她的好。李小贞就讽刺过李晓枫是个苦孩子,“因为一辈子没什么人对你好过,所以才会牢牢记得路上遇到的每一点恩情”。
记得别人的好,不对吗?
苦孩子就苦孩子,也没什么不好嘛。其实刚来广州找不到工作的那半个月她一点也不觉得苦,光顾着惊奇了,唯一惶惑的是没钱。
给周蜜一百块,再加上吃饭——那时两荤一素的盒饭是两块五毛钱,一天吃饭得五六块,李晓枫所带的钱勉强只够两三个月的花销。什么叫生活逼人,这就是生活逼人,一分一厘都打跟头翻到你面前,容不得半点含糊。她必须在这两三个月里找到工作,不然就只能回家。
没有熟人介绍,只能在人才市场里瞎找。外企国企都不在招聘季,剩下的全是二打六的小公司,就算以李晓枫当年的眼光,都能看到每一张招聘后面充满了陷阱:会打字会翻译性情温顺长相漂亮体重在五十公斤以下的总经理助理,你去吗?包食宿一万元保底加提成的酒店公关经理,你去吗?月入八千包食宿,地址在中山坑镇,你听都没听过的地方,你去吗?
在人才市场晃到第六天的时候,李晓枫是真的有点绝望了,感觉满大街都是狼,满大街都是坑,只等不谙世事的年轻女孩跳进去。若是真的不懂事倒好了,偏偏李晓枫又还略懂一点事,所以尤其觉得可怕。
最后李晓枫是靠一张皱巴巴的破报纸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在那个绝望的中午,她坐在人才市场外面的花坛边,发了半天呆,随手捡起身边一张烂报纸,鬼使神差,一眼就看到《粤城新报》的招聘启事。一看地址离人才市场不远,李晓枫心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背着包就径直走了过去。
1994年11月的广州,还是热得只能穿单衣。虽然到处乱哄哄的,但很明显看得出这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城市,到处都是人,从内地跑出来想要争取更幸福生活的人们——李晓枫想,他们和我不是一样的人吗,如果他们可以找到工作,那么我李晓枫也可以。我又不笨,我又不傻,我又不懒。
这样一想,李晓枫的心情就好多了。她哼着歌穿过了一个城中村,左右密密麻麻层层叠叠都是小盒子一样的房子,还有密如蛛网的线,把碧蓝的天空划出许多几何图案。
发廊里坐着许多穿吊带装的姑娘,倒也并没有浓妆艳抹,只是不停地对着外面的行人微笑。有一个圆脸姑娘看上去还完全是个孩子,却姿态老练纯熟地往巷子里的脏水里吐痰,隔壁士多店在昏天黑地地播刘德华的《忘情水》:“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店主在用广东话吆喝:“最平最平,今日最平……”
李晓枫就是这样单枪匹马冲进了报社,在一个乱哄哄的下午,冲进了十五楼一个乱哄哄的屋子。“谁是主编?我是来应聘的。”李晓枫问。
“欧阳,有靓女找!”有个留着长头发,歪嘴抽着烟的戴眼镜的男人眯着眼睛看了李晓枫一眼,用手指了指,“你去里面吧,欧阳在里面和人聊选题。”
李晓枫拿着毕业证书径直走了进去:“听说你们这里招人。”
屋里的四五个人愣住了。一个穿着大了两码的明显没怎么洗过的白衬衣,比李晓枫大不了两岁的男人翻看了一下她的毕业证书,说:“南湖大学的啊,师妹啊……现在只有副刊缺人。你不是懂外语吗?帮我们翻译一点外文资料呗……”这是李晓枫第一次见欧阳,一个戴着巨大方形眼镜、眼睛奇大脑袋奇大的瘦弱的湖南男人。那时他还算是一个地道的书生,没有变成“一个离过两次婚炒过无数人的无耻老板”——这评价不是李晓枫给的,是欧阳自己说的。
李晓枫这一干就是二十年。进去的时候也不是不委屈的——南湖大学的英语本科生,同学里有人进了商业部,有人进了广交会,有人去了外企——只有脑壳进了水的李晓枫,居然为了爱情跑到北京,结果三个月就大逃亡,跑到广州进了这种十三不靠没编制没名头的小报社。
当时的《粤城新报》只不过是主报旗下一个闲置了多年的小报刊号,大老板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派欧阳下去挑头,想着随便招一点年轻人做一份八卦小报挣点广告费,聊聊克林顿、邓丽君、伟哥、伊妹儿……谁知道欧阳居然带李晓枫他们这帮乱七八糟五湖四海的外乡人做成了一个名震全国的报纸,十几年之后每年的营收都上了亿,养起了整个报社。欧阳说这一切都是因缘际会,不是他有多英明,就是撞上了时运而已——他们恰好碰对了热气腾腾的九十年代,一个遍地奇迹的年代,能让一个最初只有七八个人上班的破报纸营收上亿,也能让李晓枫这种把“GUCCI”拼成“GOCCI”的穷鬼变成时尚媒体界的老行尊。
算起来李晓枫还真是看着时尚业是如何一步一步在中国兴盛起来的。品牌在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大把大把地散银子做启蒙,每隔一年或者半年就推出一个新概念,讲各种故事。他们讲故事就需要有媒体,有写手,而李晓枫恰好就在此时此刻撞了进来。
那时真是时尚业的史前时代啊,什么都没有——没有互联网,没有资料。李晓枫只好托当时在英国留学的李小贞寄资料过来——书、杂志和报纸,反正她能拾到的各种各样过期的时尚杂志和报纸。那些年全靠李小贞的海外信息支援,李晓枫才在报社立下脚跟。李晓枫把那些英文书或杂志翻译过来,再加点自己的理解,写写弄弄就是一个整版,标题是:《巴黎制衣作坊里的天才们》《为什么卡地亚是世界名牌?》……翻译是李晓枫的老本行,她学的就是英文专业,不费什么劲儿。而且最重要的是,坐在家里,不用采访,很省时间。那个时候也没有版权概念,把图扫下来,就可以赚一个版面的钱,一个整版是二百,如果都是自己写,那稿费是八百,一周四个版,一个月最少挣六千。第一个月看到工资条的时候,李晓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哪,老娘有钱啦啦啦,比外企的工资还高啊!当时内地的同学哼哧哼哧干一个月的工资她一天就挣回来了,拼命地干啊拼命地写啊拼命地挣啊,每天都乐颠颠的。
后来报纸上的文章写得多了,有出版社来找李晓枫出书。抱着挣点外快的心,李晓枫曾翻译过两本国内最早的时尚书,一本是“英国时尚女杀手”的传记,一本是伦敦女人的品牌指南。不知道为什么这两本书后来莫名其妙成了这个行业里入行必读书,所以李晓枫就莫名其妙有了一点小名气,居然成了这个虚荣圈子里最有学问的人——于是,李晓枫不留一撮毛没关系,李晓枫不涂烟熏妆没关系,李晓枫在露背派对上不露背也没有关系。每一个提起李晓枫的人会说,喔,那个写书的“温蒂·李”,那个专业的“温蒂·李”,那个早上五点钟起来写稿的老记者“温蒂·李”。
话说那天一心想摆脱北京雾霾的“温蒂·李”,也就是李晓枫本人,早早起床,准备离京。
正好周日,二环路上一路畅通,居然早早就到了。李晓枫披着她那第一百零一件巴宝莉风衣威风凛凛第一个登机了。上飞机把行李和大衣都交给空姐,里面她早已穿好自己最舒服的一套厚底真丝家居服,然后再戴上入睡利器——一只墨绿色的宽边真丝眼罩,李晓枫准备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蒙头大睡。
迷迷糊糊要入睡的时候,隔壁突然有了响动,而且响动很大。平时很少有人在头等舱里这么重重地放行李,大声叫空姐倒茶的。空姐急急地跑过来,问:“胡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这个男人问:“你们的拖鞋呢?”拖鞋就在前面的鞋袋里,他就是想享受空姐给他穿鞋的那一分钟的快感吧,李晓枫心想,这男人可真够猥琐的。
原本期待飞机快点起飞,这个猥琐男会消停一点,可是碰到限流,飞机一直没有起飞。这个男人半躺下之后居然就打开微信听语音。这种A30空客头等舱的座位上有一个罩,两人一排,声音全窝在里面。于是乎,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就在离李晓枫不到十厘米的地方不断地响起——广东话,带着长长的气音:
“哼,我唔去,人底唔去,除非你来接我啦。”
“哎呀,咯个地方不好食,咯次你不记得了,我们点咯蒂牛排根本就咬唔烂……”
“我好中意咯只LV啊,在BB出来之前,你至少一个月要比我一只中意唧包,达唔达……”
“不好嘛,不好嘛,好咸湿啊你,人底不中意……”
……
人类这种生物吧,一旦进入交配期就会十分愚蠢,这种对话如果只发生在伴侣两个人之间,十分甜蜜,一旦被不相干的人听到,就是一出恐怖剧。李晓枫听得汗毛都竖了起来,但手机的主人似乎已沉浸在年轻女声制造的粉红色荷尔蒙大阵里,意犹未尽地把这些话听了一遍又一遍。天哪,这都什么素质啊!李晓枫拉起眼罩想看一下是何方神圣。她这一看不打紧,差点没震得坐起来——天!隔壁这个猥琐男,居然是大胡。
是的,就是李晓枫的上铺——南湖大学外语系美女周蜜的暴发户老公大胡,他的左颊有一个花生形的胎记,全世界独一无二。